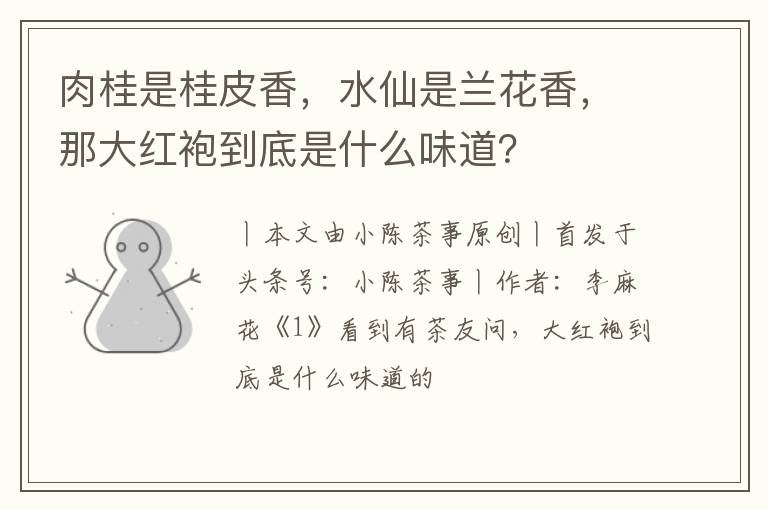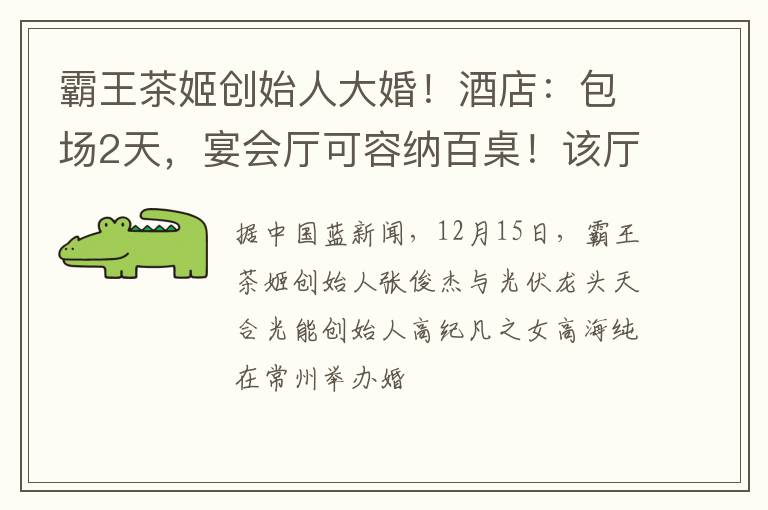婆婆把我养三年的狗送人,我一夜没睡,次日她珍藏的茶叶全成花肥
雨下了一整夜。
潮气像无形的藤蔓,顺着窗缝爬进来,缠住我的脚踝。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眼前是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城市模糊的霓虹,被雨水冲刷成一片片流动的色块。
身侧的狗窝是空的。
年糕的食盆和水碗,干干净净地放在角落,像两只沉默的眼睛。
我维持着这个姿势,已经五个小时了。
从我下班回家,发现年糕不见了,到婆婆刘兰从厨房里端出一碗汤,轻描淡写地说:“哦,年糕啊,我送人了。”
她说:“你表姨那个远房亲戚,家里有个大院子,喜欢狗,我寻思着比在我们这小鸽子笼里强。”
她说:“一条土狗,养这么金贵干嘛,你跟周成都备孕两年了,家里有这些,不干净。”
每一句话,都像一根冰冷的针,扎进我的耳膜。
我没有说话。
我甚至没有看她,目光一直落在那只空荡荡的狗窝上。
三年前,我从流浪动物救助站把年糕带回来。
它是一只普通的中华田园犬,瘦骨嶙峋,眼睛里全是怯生生的光。
是我一勺一勺喂羊奶粉,一夜一夜地陪着,才把它养到如今油光水滑,见谁都摇尾巴的模样。
它叫年糕,因为它来的那天是腊月初八,我正在喝一碗甜糯的腊八粥。
周成,我的丈夫,当时是笑着同意的。他说:“挺好,给家里添点生气。”
他知道,我们结婚五年,备孕两年,我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医院的检查报告说,我的身体底子有些寒,受孕几率偏低,但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这句话,像一张无形的判决书,贴在我们婚姻的墙壁上。
年糕的到来,填补了某种巨大的空虚。
它是我沉默的伙伴,是我情绪的出口,是我在这个冰冷房子里,唯一能抱在怀里取暖的活物。
现在,它不见了。
被我的婆婆,用一种处理一件旧家具的口吻,轻描淡写地,“送人了”。
周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
他带着一身酒气和疲惫,看到客厅里不开灯的我,吓了一跳。
“怎么了这是?灯怎么也不开?”
他伸手去按开关,被我制止了。
“别开。”我的声音很哑。
他顿住了,借着窗外的微光,终于看到了那个空着的狗窝。
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年糕呢?”
“妈送人了。”我陈述,不带任何情绪。
周成沉默了。
这种沉默,比任何辩解都更让我心寒。
他走到我身边,想抱我,我侧身躲开了。
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
“老婆,妈也是为了我们好……她那个人,思想比较旧,总觉得狗对孩子不好……”
“我们有孩子吗?”我问。
他再次沉默。
“周成,那不是一条狗。”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那是我半条命。”
他眼里的愧疚一闪而过,随即被一种更深的疲惫所取代。
“林舒,你别这样,我最近真的很累,公司项目压力大,我……”
“我知道。”我打断他,“我知道你累。”
两天前,我还不是这样。
两天前,我还相信我们的婚姻只是生病了,吃点药,打打针,总会好起来。
那天是个周六,阳光很好。
我提前下班,想给他一个惊喜,顺便把家里彻底打扫一遍。
他的手机就放在床头充电,屏幕亮着,是一个出行软件的推送。
我无意间瞥了一眼。
推送消息下面,有一行小字:“您的常用同行人‘小安’已更新行程。”
小安。
很亲昵的备注。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
我没有动他的手机。这是我的底线,也是我身为律师的职业习惯——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不打草蛇。
我只是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然后,我用自己的手机,打开了他的出行软件账号。我们是家庭共享账号,这是他为了方便我给他报销出差票据,主动绑定的。
我点开“同行人”那一栏。
“小安”的名字赫然在列。
点头像,是一张模糊的侧脸,一个年轻女孩,在阳光下笑得很甜。
系统记录冰冷而精确:近三个月,共同出行记录,二十一次。
目的地,大多是邻市。
时间,大多是周末。
而那些周末,他告诉我的版本是:去邻市见客户,开项目推进会,加班。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冰凉。
原来他口中的那些疲惫,那些负担,那些深夜不归的理由,都分了一半,甚至更多,给了另一个人。
我关掉手机,继续打扫卫生。
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把床单被套换成他最喜欢的灰色系,把他的衬衫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
我像一个精密的机器,执行着所有“妻子”该做的程序。
只是心里有个地方,塌了。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只是在等。
等一个契机,一个可以把所有问题摆上台面,一次性解决的契机。
我没想到,这个契机,是年糕的消失。
“周成,”我从沙发上站起来,五个小时的静坐让我的腿有些发麻,“你今晚睡书房。”
他愣住了,“林舒,为了一条狗,你至于吗?”
“至于。”
我看着他,“这不是一条狗的事。这是在告诉我,在这个家里,我的东西,我的感受,我这个人,都是不重要的。随时可以被牺牲,被处理。”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他的声音也提高了,“我妈她年纪大了……”
“年纪大,不是可以随意践踏别人底线的理由。”
我转身,走向卧室,关门,落锁。
门外,是他压抑的叹息和来回踱步的声音。
这一夜,我没有睡。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一遍遍地过着这五年的婚姻。
像放电影,一帧一帧,清晰无比。
那些他加班时我独自吃下的外卖,那些我深夜高烧时他关机的电话,那些纪念日里他敷衍了事的礼物,那些我从医院拿着检查报告回来时他故作轻松的安慰。
还有,那二十一次,和“小安”的共同出行。
所有的细节,在此刻串联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指向一个结论:这场婚姻,早已千疮百孔。
天亮时,雨停了。
我拉开窗帘,晨光熹微,空气里有雨后泥土的清新味道。
我走出卧室。
周成大概是后半夜回了书房,客厅里空无一人。
婆婆刘兰还没起。
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温水,然后,目光落在了客厅角落的那个红木柜子上。
柜子里,是婆婆的“命根子”。
她珍藏的各种茶叶。
大红袍,金骏眉,正山小种,还有一罐她托人从武夷山带回来的,据说有市无价的陈年老茶。
她每天最享受的时刻,就是用她那套紫砂茶具,慢悠悠地泡上一壶,然后坐在阳台上,眯着眼品。
她说,这比儿子儿媳靠谱,至少不会惹她生气。
我走过去,打开柜门。
茶香扑鼻而来。
我拿出那罐最金贵的陈年老茶,掂了掂,分量很足。
然后,我拿着它,走向阳台。
阳台上,种着几盆婆婆精心侍弄的兰花。
我拧开茶叶罐的盖子,深吸了一口那醇厚的茶香。
然后,我手一斜,把那一罐凝聚了岁月和金钱的茶叶,悉数倒进了兰花的花盆里。
褐色的茶叶,均匀地覆盖在湿润的泥土上。
像一层昂贵的肥料。
我做完这一切,内心平静无波。
这不是冲动,是计算。
是你破坏了我的珍爱之物,我就毁掉你的心头之好。
这是一场等价交换。
也是一场宣战。
上午九点,婆婆起床了。
她哼着小曲,习惯性地走向她的红木柜,准备开始她雷打不动的早茶仪式。
下一秒,她的惊叫声刺破了整个屋子的宁静。
“我的茶!我的茶叶呢!周成!林舒!”
周成从书房里冲出来,“妈,怎么了?”
“我的那罐老茶!不见了!”刘兰的声音都在发抖,指着空了一格的柜子,脸色惨白。
我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牛奶,慢条斯理地喝着。
“我倒了。”我说。
空气瞬间凝固。
刘兰和周成,两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你说什么?”刘兰的声音尖锐得像要划破玻璃,“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把你那罐茶叶,倒了。”我走到阳台边,指了指那几盆兰花,“喏,在那儿,当花肥了。听说茶叶做肥料,养花特别好。”
刘兰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当她看到那些覆盖在泥土上的茶叶时,她整个人晃了一下,几乎要站不稳。
周成赶紧扶住她。
“林舒!你疯了!”周成对我怒吼,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我没疯。”我看着他,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只是在教妈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一个成年人都该懂的道理: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碰。”
刘兰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把矛头对准了周成。
“周成!你看看你娶的好老婆!她这是要反天了!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就是这么让她来糟践我的?我的茶啊……那是我托了多少关系才弄来的……”
她开始哭,一边哭一边捶打周成。
周成一脸的焦头烂额,一边安抚他妈,一边用一种极其失望和愤怒的眼神看着我。
“林舒,你必须给妈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反问,“她把我的年糕送人,她道歉了吗?”
“那能一样吗?那是一条狗!这是多贵的茶叶!”
“在我这里,一样。”
我放下牛奶杯,杯子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我的世界里,年糕的价值,远比那罐茶叶贵重。如果你不能理解,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你……你简直不可理喻!”
“这就不可理喻了?”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周成,我们之间,还有更不可理喻的事情,需要谈谈。”
我拿出手机,点开那张我早已截好的图。
“常用同行人,小安。”
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他。
周成的脸色,瞬间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
他眼里的怒火,在看到那个名字和头像的瞬间,迅速熄灭了,取而代代的是一种被戳穿的恐慌。
刘兰的哭声也停了,她显然没看懂屏幕上的内容,但她看懂了自己儿子的表情。
“什么东西?”她狐疑地问。
我没理她,只是盯着周成。
“需要我解释一下,这个‘常用同行人’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过去三个月里,你有二十一个周末,是和这位‘小安’小姐一起度过的。”
“而你告诉我,你在加班,在出差,在为这个家奔波。”
我每说一个字,周成的脸色就更白一分。
“周成,你累吗?”我问他,声音很轻,“两头跑,编两套说辞,维持两个世界,一定很辛苦吧?”
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刘兰终于反应过来了,她一把抢过我的手机,凑近了看,然后,她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尖叫。
“这……这是什么?周成!这个女人是谁!”
客厅里,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
刘兰的哭喊,咒骂,周成的辩解,搪塞,混杂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烂粥。
“妈,你别听她胡说!就是个同事!项目上的同事!”
“同事?同事能每周都一起出去?你当妈是傻子吗!”
我冷眼旁观。
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看着舞台上一出荒诞的闹剧。
我没有兴趣参与进去。
我等他们吵。
等他们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
终于,刘兰哭累了,坐在沙发上喘气。
周成也放弃了辩解,颓然地靠在墙上,额头上全是冷汗。
客厅里,只剩下压抑的喘息声。
“说完了吗?”我开口,打破了死寂。
两人都看向我。
“说完了,就该谈谈正事了。”
我从我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打印好的文件,放在茶几上。
文件最上面,用黑体三号字,清晰地写着五个字:
《婚内财产协议》
周成的瞳孔猛地一缩。
刘兰不识字,但她能感觉到那份文件的分量,以及我此刻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不容置喙的冰冷气场。
“林舒,你这是什么意思?”周成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字面意思。”
我拉开一张椅子,坐下,姿态像是在谈判桌上,而不是在自己家的客厅。
“周成,我们结婚五年。婚后,我们共同购买了这套房子,一辆车。你的年收入,是我的三倍。我们的共同存款,由你母亲代为保管,美其名曰‘理财’。”
我看着刘兰,“妈,对吗?”
刘兰的脸色很难看,但还是点了点头。
“现在,我需要重新明确一下我们婚姻内部的权责利。”
我把文件推到周成面前。
“第一,这套房子,购房时我父母出资30%,你父母出资20%,我们共同贷款50%。房产证上,必须加上我的名字。三天内办完。”
“第二,家里的所有存款,包括你妈‘理财’的那部分,必须转入我们两个人的联名账户,由我们共同管理。任何超过一万元的支出,必须经由双方共同签字同意。”
“第三,”我的目光变得锐利,“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关于‘忠诚义务’。”
“协议里明确规定,婚内任何一方,与第三方发生超越正常同事、朋友界限的情感或肉体关系,即视为违约。”
“违约方,将自动放弃所有婚内共同财产的分割权,净身出户。并且,需要向守约方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金额为违约方年收入的三倍。”
周成的脸,已经毫无血色。
刘兰听得一知半解,但“净身出户”四个字,她听懂了。
“你这是抢劫!”她尖叫起来,“凭什么!我儿子辛辛苦苦赚的钱,凭什么都给你!”
“凭什么?”我看向她,一字一顿,“凭我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妻子。凭他对我,对这段婚姻,首先负有忠诚的义务。”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周成。”我把视线转回我的丈夫身上,“我是在通知你。”
“签,或者,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么,我会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份出行记录,以及其他我还没有拿出来的证据,会成为法官判定你为过错方的有力证明。到时候,财产怎么分,就不是你我说了算了。”
我把一支笔,放在协议旁边。
“你选。”
整个客厅,安静得能听到墙上石英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滴答,滴答。
每一下,都像敲在周成和刘兰的心上。
周成看着那份协议,手在抖。
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是一个律师。
我从不做没有准备的仗。
我说到,就一定会做到。
刘兰还想说什么,被周成一个眼神制止了。
他知道,他母亲再说下去,只会让情况更糟。
他慢慢地拿起那支笔,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有落下。
“林舒,”他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声音嘶哑,“一定要这样吗?我们五年的感情……”
“感情?”我笑了,“当你在周末带着‘小安’去邻市看风景的时候,你在想我们的感情吗?”
“当你母亲,随意处置我的年糕,把它从我身边夺走的时候,你在维护我们的感情吗?”
“周成,别跟我谈感情。感情太虚了,我抓不住。”
“我现在,只相信白纸黑字,相信条款,相信违约责任。”
“婚姻如果不能保证爱,那至少,要保证我的利益。”
他闭上眼,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在协议的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周成。
那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力透纸背。
我拿起协议,吹了吹上面的墨迹,仔细地收进我的公文包里。
一式两份,另一份,我留在了茶几上。
“好了。”我站起来,“第一件事,现在,立刻,马上去把年糕给我找回来。”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你表姨的远房亲戚也好,报警也好。天黑之前,我要见到年糕,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这份协议,立刻生效。我们法庭见。”
说完,我转身回了卧室,再次,关门,落锁。
我知道,门外,是这对母子兵荒马乱的一天。
而我,需要补觉。
这一觉,我睡得格外沉。
没有梦。
醒来时,是下午四点。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我走出卧室。
客厅里,刘兰不在。
周成坐在沙发上,神情憔悴,像一棵被霜打过的茄子。
听到我开门的声音,他抬起头,眼神复杂。
“找到了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找到了。”
“妈去乡下亲戚家了,我开了一天车,刚把年糕接回来。在宠物店洗澡,一会儿就送过来。”
“嗯。”我应了一声,走进厨房,给自己倒水。
他跟了进来,靠在门框上。
“林舒,我们能……谈谈吗?”
“我们不是已经谈完了吗?”我喝着水,没有看他。
“那不是谈,那是你在审判我。”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
我放下水杯,转过身,看着他。
“好。那我们现在谈。”
“为什么?”我问,“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还是,你觉得我们的婚姻,已经让你无法呼吸了?”
他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开口。
“不是你不好。你很好,太好了。”
“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工作上独当一面,你冷静,理智,强大得像一个女战士。跟你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很累。”
“我累?”我几乎要气笑了,“周成,你觉得我累?”
“不,是我累。”他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觉得在你面前,我像个透明人,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喘不过气。”
“所以,你就去找一个能让你喘得过气的?”
他痛苦地闭上眼。
“安可她……她很年轻,刚毕业的实习生,什么都不懂。她很崇拜我,觉得我什么都懂,什么都能搞定。”
“在她面前,我感觉自己很有价值,很有成就感。我能找到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我静静地听着。
这就是男人。
永远在寻找一个能满足他英雄主义幻想的舞台,一个能让他感觉自己“被需要”的观众。
“所以,你爱她吗?”我问出了那个最俗气,也最核心的问题。
他睁开眼,眼神里满是挣扎。
“我不知道……我只是……贪恋那种感觉。”
“贪恋?”我重复着这个词,“周成,你今年三十四岁了,不是十四岁。成年人的世界里,每一个行为,都要承担后果。”
“我知道。”他低下头,声音闷闷的,“林舒,对不起。”
“对不起这三个字,是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平视着他。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家,这段婚姻,你还要不要?”
他猛地抬起头,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我的手。
“要!我当然要!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他的手很用力,掌心全是汗。
“我错了,林舒,我真的错了。我跟她,我会断干净。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看着他眼里的惊慌和恳求,那不是演出来的。
他是真的怕了。
怕失去我,失去这个家,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抽回我的手。
“机会,不是靠嘴巴说的。”
“协议你签了。从今天起,我们的一切,都按照协议上的条款来。”
“你的工资卡,上交。你的手机,我可以随时检查。你的行程,必须提前一天向我报备。”
“我不是在囚禁你,我是在帮你建立规则感。”
“周成,信任一旦被打破,想要重建,靠的不是感情,是制度。”
他愣愣地看着我,像是不认识我一样。
“你好像……变了。”
“是吗?”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没变。我只是把我原来用来爱你的精力,拿回来,用来保护我自己了。”
“以前,我以为婚姻是避风港。现在我明白了,婚姻就是战场。而我,不能再赤手空拳了。”
门铃响了。
是宠物店的人,把年糕送了回来。
我打开门,一股熟悉的,沐浴露的香气扑面而来。
“年糕!”
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一见到我,就兴奋地扑了上来,用它的舌头,疯狂地舔我的脸。
我抱住它,紧紧地抱住。
把脸埋在它温暖的,柔软的毛发里。
那一刻,我强撑了两天一夜的堤坝,终于决堤了。
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年糕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悲伤,它不动了,只是安静地趴在我怀里,用它的头,轻轻地蹭我的下巴。
周成就站在我身后,看着我抱着狗,哭得像个孩子。
他想上前,又不敢。
我抱着年糕,回了卧室。
晚餐,是周成做的。
三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他把饭盛好,递给我。
“妈她……回老家了。她说,她想清静清静。”
“嗯。”
“她说……对不起年糕。也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默默地吃饭。
“茶叶的钱,我明天转给你。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不用了。”我说,“我对茶叶没兴趣。我只是,不喜欢我的东西被人碰。”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沉默。
年天就趴在我的脚边,时不时用头蹭蹭我的小腿。
吃完饭,周成默默地收拾碗筷。
然后,他把他的工资卡,身份证,车钥匙,都放在了茶几上。
“以后,家里的钱,都归你管。”
他还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这是新的开机密码,你的生日。”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去拿手机。
“周成,我不是要当一个狱警。”
“我知道。”他苦笑了一下,“是我自己,需要一个手铐。林舒,我是心甘情愿的。”
那天晚上,他没有再回书房。
他睡在了卧室的地上,给我和年糕守夜。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和年糕轻微的鼾声。
心里,空落落的。
我知道,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即便用再好的胶水粘起来,裂痕也永远都在。
接下来的日子,很平静。
周成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戒了烟,戒了酒。
每天准时下班,回家就钻进厨房。
他的手机,大大方方地放在任何我能看到的地方。
每周,他会主动把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给我看。
我一次都没看过。
但他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他开始学着照顾年糕,给它梳毛,带它散步。
年糕似乎也接纳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粘着我一个人。
家里的气氛,从冰点,慢慢回温。
像冬末初春,冰雪开始消融,但空气里,依然带着寒意。
有一次,我妈来看我。
她拉着我的手,悄悄塞给我一个东西。
是一个温润的玉坠。
“这个,你戴着。保平安,也保你们夫妻和睦。”
她看着我,语重心长,“舒舒啊,过日子,就像这玉,要慢慢养,才能润。男人嘛,偶尔犯点错,只要他知道回家,就得给他个台阶下。水至清则无鱼,懂吗?”
我摸着那块冰凉的玉,没有说话。
我懂我妈的意思。
她是那个时代的女人,信奉的是“忍”和“熬”。
但我不行。
我的世界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
忠诚不是选择,是底线。
我把玉坠收下了,但没有戴。
我更相信我公文包里那份签了字的协议。
玉,太脆弱,易碎。
而白纸黑字,坚硬,冰冷,但可靠。
一个月后的一个周五。
我正在加班,整理一个案子的卷宗。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我点开。
上面只有一句话。
“林律师,你好。我是安可。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我看着那条短信,手指停在屏幕上。
窗外,夜色正浓。
我知道,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