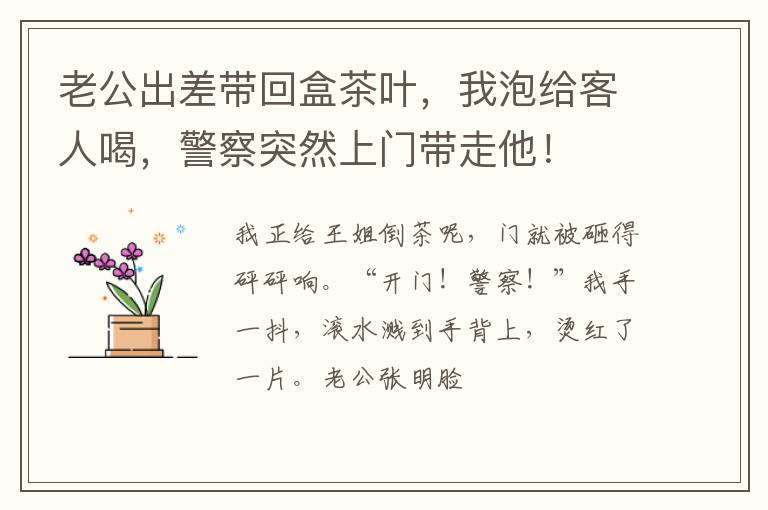
我正给王姐倒茶呢,门就被砸得砰砰响。
“开门!警察!”
我手一抖,滚水溅到手背上,烫红了一片。老公张明脸色唰地白了,刚才还跟客人吹牛呢,这会儿屁股像粘在沙发上。
“谁啊这是……”王姐端着茶杯,有点慌。
我去开门,两个穿警服的进来,眼神跟刀子似的,直接扎向张明。“张明是吧?跟我们走一趟。”
“凭……凭什么啊?”张明站起来,腿有点抖,声音倒是挺大,“我犯什么事了?”
“什么事?”高个警察冷笑,指了指茶几上那盒拆开的茶叶,“就为这个。有人举报,你携带违禁品。”
王姐“哎哟”一声,赶紧放下杯子,好像那杯子咬手。
我脑子嗡了一下:“警察同志,搞错了吧?这就是普通茶叶,我老公出差带回来的……”
“普通?”另一个警察已经戴上手套,小心地捏起一小撮墨绿色的茶叶,放在鼻尖闻了闻,又对着光仔细看。“里面掺了东西。具体是什么,回去化验才知道。张明,别磨蹭。”
张明被带走了,临走前回头看我那一眼,全是怨毒,好像是我举报的他。门关上,屋里死静。王姐干巴巴地说:“小陈啊,那我……先走了?家里还有点事。”
我送她到门口,她连句客套话都没说,逃似的进了电梯。
我看着那盒茶叶,包装挺讲究,深蓝色铁盒,上面印着看不懂的外地书法。张明昨晚才回来,丢给我时说:“客户给的,好茶,留着招待人。”
我泡茶时是觉得香味有点冲,不像平常的绿茶清香。可我没多想。张明经常出差,带回来的东西杂七杂八,我从来不过问。
手机响了,是婆婆,嗓门大得炸耳朵:“陈芳!怎么回事?我儿子怎么被警察抓了?你是不是又惹什么事了?”
“妈,是茶叶有问题,警察说他带了不该带的……”
“放屁!”婆婆打断我,“我儿子最老实!肯定是你!是不是你往茶叶里乱放了什么,想害他?我早看出来你心思不正!”
我张了张嘴,没出声。挂了电话,手还在抖。不是气的,是空的。
晚上,我去了派出所。警察不让见人,只说了情况。茶叶里掺了一种新型致幻剂原料,磨碎了混在茶叶里,很难分辨。量不大,但性质恶劣。张明咬死了不知情,说是客户给的,他当普通礼物收的。
“哪个客户?联系方式?”警察问。
张明支支吾吾,说名片丢了,就饭桌上见过一次,姓李。
警察看我的眼神带着审视:“你一点不知情?”
我摇头。真不知道。我和张明结婚五年,话越来越少。他在外跑销售,我在公司做会计。他赚得比我多,家里开销大半靠他,气也越来越粗。我习惯了沉默,习惯了把他带回来的东西收好,不同、不碰、不管。
回到家,冷锅冷灶。手机不停响,亲戚、邻居,名义上是关心,话里话外都在打听:“张明真贩毒啦?”“哎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小陈你可得想想办法,不然你也说不清。”
我谁也没回。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找张明公司。他上司老刘见了我,一脸为难:“小陈啊,张明这事……影响太坏。公司正在评估。他那趟出差,见的什么客户,公司备案不详细。现在警方调查,我们也很被动。”
“刘总,他出差报销单据,能让我看看吗?或许能找到点线索。”
老刘犹豫了一下,大概觉得我也可怜,让助理调了记录。我一眼就看到问题:出差地点是云南一个边境小城,但报销的餐饮发票金额高得离谱,一顿饭两千多。张明一个销售,请客户吃这么贵?
我记下了发票上的饭店名字。
晚上,婆婆带着小姑子直接杀到我家。小姑子张丽一进门就嚷嚷:“嫂子,哥这事你必须负责!赶紧找关系把人弄出来!不然我哥前途毁了,你也别想好过!”
婆婆一屁股坐沙发上,拍着大腿哭:“我苦命的儿啊……娶了个丧门星啊……家里一点忙帮不上,净拖后腿!”
我看着她们,没倒水,也没坐。“警察在查。清白的,自然会出来。”
“查?等他们查出来我儿子都完了!”婆婆指着我的鼻子,“你拿钱啊!你不是攒了私房钱吗?去找人!送礼!托关系!这还要我教?”
“我没钱。”我说的是实话。工资卡在张明手里,他说他理财,我每月就一点生活费。
“你没钱?”张丽尖声笑起来,“谁信啊!你肯定藏了!不想帮我哥是吧?心真毒!”
她们闹到很晚才走,留下满地狼藉。我慢慢收拾,心像泡在冰水里。
又过了两天,警察通知我去一趟。还是那个高个警察,姓赵。他脸色更严肃了。“陈芳,我们查了张明的银行流水。最近三个月,有多笔不明大额收入,加起来二十多万。解释不清。而且,”他顿了顿,“我们排查了他的通讯记录,发现他和一个境外号码联系频繁。最后一次通话,就在他被抓前一天。”
我耳朵里嗡嗡响。“境外?”
“对。我们怀疑,他可能不止是‘不知情’收了问题茶叶那么简单。”赵警察盯着我,“你作为妻子,真的一点异常没发现?”
我用力回想。张明最近是有点怪,总背着我接电话,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次我半夜起来,看见他在阳台抽烟,对着手机发呆。我问过,他说工作压力大。
我还真信了。
“他……他好像很缺钱。”我慢慢说,“前阵子提过,想换车,还说有个投资机会,稳赚。”
“什么投资?”
“他没细说,我就没问。”
赵警察叹了口气,不知是失望还是什么。“案子升级了。你暂时不能见他。另外,家里可能还有类似东西,你仔细找找,有发现立刻通知我们。”
我浑浑噩噩回到家,开始翻找。张明有个旧行李箱,常年锁着,放在衣柜顶层。我从来没碰过。今天,我搬了凳子,把它拿下来。锁是密码锁,我试了他生日、婆婆生日、结婚纪念日,都不对。最后,我试了我的生日。
“咔哒。”开了。
我愣住了。心里那点冰,裂开缝,冒出刺骨的寒气。
箱子里没什么特别,几件旧衣服,一些杂物。底下压着一个硬皮笔记本。我翻开,前面记着些工作琐事。翻到后面,字迹变得潦草,内容让我手脚冰凉。
“李老板说这次‘茶叶’成色好,价钱翻倍……风险大,但来钱太快了。”
“芳好像有点疑心,得小心。这傻女人,好糊弄。”
“妈又催生儿子,烦。钱还没攒够,换大房子再说。芳身体不好,怀了也麻烦,不如不要。”
“丽想买新款包,当哥的得表示。反正现在来钱容易。”
“最后一次,干完这笔就收手。够本了。”
笔记本最后几页,是一些数字和代号,我看不懂,但直觉不是好东西。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名片,上面只有一个“李”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正是警察说的境外号码。
我坐在地上,浑身发冷。原来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把那些脏东西带回家,让我泡给客人喝。他拿命换钱,还在本子上写我“好糊弄”。婆婆催生,他嫌我身体不好麻烦。小姑子要包,他拿脏钱去充面子。
五年婚姻,我像个傻子。
我把笔记本和名片拍照,原件放回箱子,推回衣柜顶层。然后,我打给了赵警察。
“赵警官,我找到了点东西。”我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一个笔记本,一张名片。可能对你们有用。”
“好!我们马上派人去取。你别动任何东西。”赵警官语气急促,“注意安全。另外,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包括张明的家人。”
“我知道。”
第二天,婆婆和张丽又来了,这次还带了两个我不认识的远房亲戚,男的看着挺凶。
“陈芳,今天你必须给个准话!到底能不能把我儿子弄出来?”婆婆叉着腰,唾沫星子快喷我脸上。
“警察在查,我说了不算。”
“你别拿警察搪塞!”张丽推了我一把,“你是不是巴不得我哥出不来,好独吞家产?我告诉你,没门!这房子我哥出了大头,你休想霸占!”
那个凶男人往前站了一步,眼神不善地打量着我:“嫂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明哥这事,你得使劲。不然,家里老人着急上火,出点什么事,你担待不起。”
这是威胁。
我看着他们,看着婆婆那张因为愤怒和恐惧扭曲的脸,看着小姑子那副理所当然索取的嘴脸,看着陌生人狐假虎威的架势。
“家产?”我轻轻重复,“你们知道张明可能做了什么吗?他带回来的茶叶里有什么吗?那不是小事,搞不好要坐很多年牢。”
“那又怎样?”婆婆尖叫,“他是我儿子!是你丈夫!你不想办法救他,还有脸说风凉话?你个没良心的!”
“就是!”张丽帮腔,“我哥赚钱养家的时候你怎么不嫌?现在出事了就想撇清?做梦!”
“赚钱养家?”我抬起头,第一次直直地看着婆婆的眼睛,“妈,他赚的什么钱,您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吗?他笔记本里写了,最后一次,干完就收手。他干的是什么,您猜不到吗?”
婆婆的脸色瞬间僵住,张狂的气焰卡在喉咙里。
“你……你胡说什么?什么笔记本?”
“警察已经拿走了。”我说,“里面记得很清楚。他和境外的人做生意,做的不是正经生意。那些钱,不是提成,是脏款。”
“你放屁!”张丽脸色发白,还在强撑,“我哥不是那种人!肯定是你诬陷!”
“是不是,警察会查清楚。”我走到门口,拉开门,“你们走吧。我这里,没有你们要的钱,也没有办法。法律说了算。”
“你敢赶我们走?”凶男人想冲过来。
“这是我家。”我没动,“你再往前一步,我立刻报警。正好,让警察听听,你们是不是知道内情,是不是在包庇,或者,”我顿了顿,“是不是也参与了分钱。”
这句话砸下来,屋里死寂。婆婆的嘴唇哆嗦着,惊恐地看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张丽也吓住了,眼神躲闪。
那凶男人啐了一口:“晦气!”转身走了。
婆婆和张丽灰溜溜地跟了出去,没再说一句话。
门关上,世界清静了。我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在地上。没有哭,只是累,骨头缝里都透着累。
几天后,赵警官联系我,说根据笔记本和名片线索,他们顺藤摸瓜,破获了一个跨境走私违禁药物的团伙,抓了好几个人。张明在其中角色不轻,不止是运送,还参与了联系和分销。证据确凿,等着公诉。
“案子基本清楚了。”赵警官说,“多亏了你提供的线索。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该怎样就怎样。”我说。
我提出了离婚。张明在里面暴跳如雷,传话出来骂我落井下石,不得好死。婆婆那边再没动静,听说吓病了,也没脸再来闹。
房子是婚后买的,虽然张明出的首付多,但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他的非法所得会被追缴,剩下的,该我的,我一点没让。请了律师,慢慢打官司。
我没要他的脏钱买来的任何东西。收拾自己衣物离开那天,我又看到了那个茶叶盒子,还摆在茶几上,像个丑陋的纪念碑。
我拿起它,走到楼下垃圾桶,扔了进去。
回头看了看那个曾经叫做“家”的窗户,心里空荡荡,但也松了一下,像卸掉一块锈死沉沉的铁。
后来,听说张明判了。刑期不短。
我没有去听宣判。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小单间,朝南,阳光很好。周末偶尔和朋友喝喝茶,是真的茶,清透的,滚烫的,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
朋友有时会小心翼翼提起过去,我摇摇头,说都过去了。
真的过去了。那盒茶叶的苦涩,好像都留在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客厅里。而我的日子,像杯中新沏的茶,热气袅袅,味道淡了,却也干净了。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