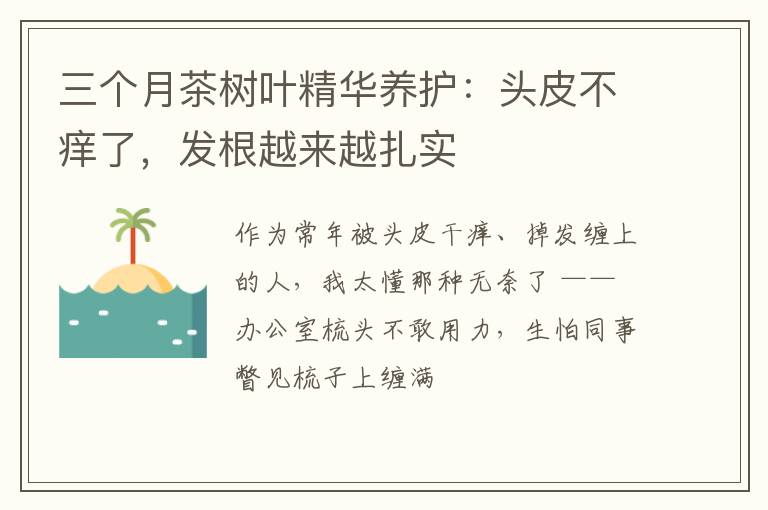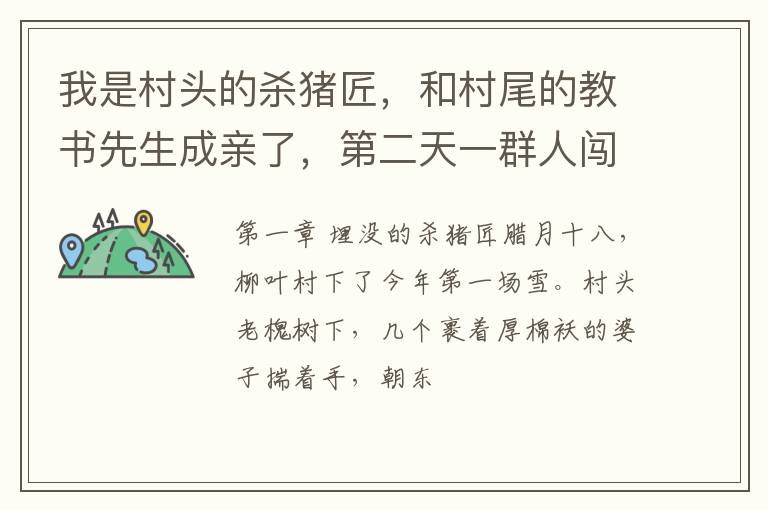
第一章 埋没的杀猪匠
腊月十八,柳叶村下了今年第一场雪。
村头老槐树下,几个裹着厚棉袄的婆子揣着手,朝东头那间贴着褪色红纸的土坯房努嘴。
“真成了?屠娘嫁了那苏先生?”
“可不嘛,昨儿个拜的堂。啧啧,你是没瞧见,新娘子一身猪骚味儿,拜堂前还在后院杀了两头猪呢!”
“哎哟,那苏先生可是读书人,咋想的?”
“穷酸配瘟神呗……”
话音没落,土坯房的门开了。

我拎着两扇刚剁好的猪排骨走出来,棉袄袖口挽到手肘,露出的小臂上还有一道陈年刀疤。雪落在热腾腾的排骨上,滋滋地响。
那几个婆子立马闭了嘴,眼神躲闪着散了。
我当没看见,把排骨挂到屋檐下的铁钩上。血水顺着骨缝往下滴,在雪地里砸出一个又一个小红坑。
是,我是柳叶村的杀猪匠,叶屠娘。
昨日嫁的,是村尾那个穷教书先生,苏文轩。
这门亲事,村里人笑掉了大牙。说一个是满手血腥的屠户,一个是酸腐穷书生,绝配。
他们不知道,十年前,我不叫叶屠娘。
我叫叶青梧。
是北境军中,唯一的女将军。
“屠娘!”
院外传来喊声。是王婶,西头做豆腐的。她挎着个篮子,深一脚浅一脚踩雪过来,从篮子里掏出两方用油纸包好的豆腐。
“刚点的,还热乎。你和苏先生……凑合吃。”
我接过来,豆腐还烫手。
“谢了,王婶。”
这是十年来,唯一一个不躲着我、肯跟我说话的村里人。
“谢啥。”王婶压低声音,往院里瞅了眼,“苏先生……人还好吧?昨儿夜里没闹腾?”
我知道她问什么。
村里都说我命硬,克亲。爹娘死得早,前头说过两门亲,一个还没过门就摔断了腿,另一个听说要娶我,连夜跑了。
苏文轩是第三个。
“挺好。”我说,“睡得踏实。”
王婶松了口气,又絮叨几句,转身走了。
我拎着豆腐回屋。
屋子是爹娘留下的,三间土房,我住东间,西间原来堆杂货,如今收拾出来给苏文轩。中间是堂屋,摆着一张瘸腿的方桌,两条长凳。
苏文轩正坐在桌边看书。
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听见我进来,抬起眼,冲我点了点头。
“有劳。”
声音温润,像他这个人。
我把豆腐放到灶间,生火,烧水,切了半棵白菜。又从檐下取下一块五花肉,洗净,切成薄片。
刀是杀猪刀,一尺来长,刃口雪亮。
这刀跟了我十年。杀过猪,也杀过人。
肉片下锅,刺啦一声,油烟腾起。我熟练地翻炒,加盐,加酱,最后把白菜豆腐倒进去,添水,盖上锅盖。
灶膛里的火噼啪作响。
我盯着那火苗,有些出神。
十年前,北境,雁回关。
也是这样的冬天,雪比这大得多。我在军帐里看地图,副将沈云舟端来一碗热汤。
“将军,趁热喝。”
我接过,汤里飘着几片肉,是今天打到的野兔。
那时候,我叫叶青梧,是朝廷正四品明威将军,统领北境左军三万兵马。爹是已故的镇北侯,叶家世代守边。
我以为,我会像我爹一样,一辈子守着那道关。
直到那个晚上。
“屠娘?”
苏文轩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锅里的水沸了,咕嘟咕嘟顶着锅盖。我揭开盖,白气扑面,熏得眼睛有点湿。
“马上好。”
我把菜盛到粗陶盆里,端上桌。又盛了两碗糙米饭,递给他一碗。
两人对坐,默默吃饭。
苏文轩吃相很斯文,一小口一小口,细嚼慢咽。我吃得快,三两口扒完半碗,抬头看他。
他长得确实好看。
眉眼清俊,鼻梁挺直,皮肤是读书人那种不见日头的白。不像村里那些汉子,黑糙粗壮。
可这样的人,怎么会愿意娶我?
媒人来说亲时,我正给一头两百斤的猪开膛。血糊了一手,抬头问:“啥?”
“苏先生托我来问问,姑娘可愿下嫁?”
我以为听错了。
苏文轩是三个月前来村里的。租了村尾一间破屋,开了个私塾,收七八个娃娃,教他们认字。束脩收得极低,有时几把米、几棵菜就行。
村里人说他傻。
他也确实不像个会过日子的。衣裳永远是那两件,补丁摞补丁。饭都吃不饱,还总拿铜板接济更穷的人。
可娃娃们喜欢他。
我也见过他几次。在村口,他给那些娃娃念诗,声音清朗,像山涧里的水。
我从没想过,这样的人,会跟我扯上关系。
“为啥?”我当时问媒人。
媒人支支吾吾:“苏先生说……姑娘实在,能过日子。”
放屁。
后来我才知道,是村里那些长舌妇,在苏文轩跟前嚼舌根,说我命硬克夫,这辈子嫁不出去。苏文轩听了,只说一句:“既如此,我娶。”
他就这么搬进了我这间土坯房。
带着两箱书,一身旧衣裳。
“今日,贾富贵又来要债了?”
苏文轩忽然开口。
我嗯了一声。
贾富贵是村里地主,我爹死前欠了他五两银子。利滚利,如今成了二十两。这十年,我杀猪挣的钱,大半填了这窟窿。
“还剩多少?”
“八两。”
苏文轩放下碗,从怀里摸出个旧钱袋,倒出几块碎银,推到我面前。
“这里有三两。是我这个月的束脩,你先拿着。”
我没接。
“你自己留着。束脩本就少,天冷了,该添件厚衣裳。”
“我够用。”他坚持,“先把债还了,少些利息。”
我看着他。
烛火跳动,在他眼睛里映出两点暖光。
十年了。
十年没人在意过我是不是冷,是不是饿,是不是被人逼债逼到墙角。
我别开脸,把银子收进袖袋。
“谢了。回头还你。”
“不必还。”他说,“既成了亲,便是一家人。”
一家人。
我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苏文轩去西屋看书。我刷了锅,烧了热水,拎到后院。
后院不大,墙角搭着猪圈,现在空着。另一头是杀猪的案台,木头被血浸得发黑。
我脱了棉袄,只穿单衣,从井里打上冷水,从头浇下。
腊月的井水,冰得刺骨。
我咬着牙,又浇了一桶。
十年了,我每天这么浇。冬天用冷水,夏天用井水。不是为了干净,是为了记住。
记住雁回关外那场大雪。
记住那些死在我面前的兄弟。
记住那支从我背后射来的箭。
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流进眼睛,又涩又疼。我抹了把脸,睁开眼。
月光惨白,照在杀猪刀上。
刀身映出我的脸。
一道狰狞的疤,从左眉骨斜到右脸颊,像条蜈蚣趴在那儿。
这是当年那支箭划的。
射箭的人,是沈云舟。
我最信任的副将。
“叶屠娘!”
粗嘎的喊声从前院传来。
是贾富贵。
我套上棉袄,擦了把头发,走到前院。贾富贵揣着手站在院门口,身后跟着两个家丁。
“钱呢?”他眯着眼,脸上的横肉堆出假笑,“今儿可是最后期限。二十两,少一个子儿,你这破屋就抵给我了。”
我从袖袋里掏出苏文轩给的三两,又进屋把攒的铜板都倒出来,凑了五两。
“先还这些。剩下的,下个月。”
贾富贵掂了掂银子,嗤笑:“就这点?打发叫花子呢?”
“就这些。”我说。
“那可不行。”他往前一步,身上的酒气混着油腻味儿扑过来,“要不这样,你陪爷喝两杯,爷再宽限你几天?”
他伸手要摸我的脸。
我没动。
等他手快到跟前时,我抓住他手腕,一拧。
杀猪的手,有的是力气。
贾富贵嗷一嗓子,脸都白了。
“你、你放手!”
“钱,下个月还。”我盯着他,“再动手动脚,我剁了你的爪子喂狗。”
我松开手。
贾富贵踉跄退了两步,指着我的手直哆嗦:“你、你等着!”
他带着家丁骂骂咧咧走了。
我站在院里,雪又下起来。
苏文轩从西屋出来,站在檐下看我。
“没事。”我说。
他沉默一会儿,说:“明日我去镇上,接些抄书的活。”
“不用。”
“我是你丈夫。”
“假的。”我转身往屋里走,“媒人说了,你娶我,是可怜我。等风头过了,你就走。我记着呢。”
“叶青梧。”
我脚步顿住。
十年了。
十年没听人叫过这个名字。
我慢慢转过身。
苏文轩站在雪里,青衫被风吹得鼓起。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
“我不是可怜你。”
“我娶你,是因为你是叶青梧。”
雪落无声。
我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跳得又沉又重。
“你怎么知道……”
话没说完。
院门被撞开了。
不是贾富贵。
是一队兵。
穿着黑色甲胄,腰佩长刀,靴子上沾满泥雪。为首的是个络腮胡的汉子,眼神凶狠,扫过院子,落在我身上。
“谁是叶屠娘?”
我往前走了一步。
“我是。”
汉子打量我两眼,又看向苏文轩。
“你是苏文轩?”
苏文轩上前,挡在我身前半个身子。
“正是。不知军爷何事?”
汉子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抖开。
是海捕文书。
上面画着两个人像。一个是我,十年前的我,脸上还没有疤。另一个……
是苏文轩。
“苏文轩,本名苏砚,兵部前侍郎苏明远之子。三年前私逃出京,隐匿乡野。”汉子冷笑,“至于你,叶屠娘——”
他盯着我。
“北境军前左将军,叶青梧。十年前雁回关一战,通敌叛国,致使我军大败,三万将士葬身雪原。朝廷追捕十年,原来躲在这儿。”
雪越下越大。
落在肩头,化开,冰凉一片。
我听见自己很平静地问:“所以呢?”
“所以?”汉子一挥手,“拿下!”
四个兵冲上来。
我没动。
苏文轩也没动。
就在那些兵的手要碰到我的瞬间——
“且慢。”
苏文轩从怀中掏出一块令牌。
纯金打造,在雪光里泛着冷芒。上面刻着一个字:御。
汉子脸色骤变。
“这是……”
“陛下亲赐,巡查御史令。”苏文轩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见令如见君。尔等,跪。”
噗通。
噗通。
一院子兵,全跪下了。
雪地里,黑压压一片。
苏文轩收回令牌,看向那络腮胡汉子。
“回去告诉魏忠。”
“叶将军的案子,陛下要重审。”
“至于我——”他顿了顿,侧头看我一眼,嘴角弯起一点极淡的弧度。
“我陪我夫人,在柳叶村,再住几日。”
第二章 刀尖上的往事
那队兵走了。
雪地上留下一串杂乱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盖住。
院门吱呀一声,被风吹得来回晃荡。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苏文轩——或者说,苏砚。
他背对着我,正在把那张海捕文书折好,收进袖中。动作不紧不慢,仿佛刚才只是赶走了一群聒噪的麻雀。
“巡查御史。”我开口,声音有点哑。
他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
“是。”
“三年前私逃出京?”
“假的。”他说,“是陛下密旨,让我暗中查案。”
“查什么案?”
苏文轩没立刻回答。
他走回桌边,提起炉子上烧开的水壶,往两个粗陶碗里倒水。热气腾起来,模糊了他的眉眼。
“雁回关之战。”他说。
水声咕嘟。
我手指无意识地抠进门框的木缝里。指甲盖劈了,渗出血丝,不觉得疼。
“陛下……不信我通敌?”
“从来不信。”苏文轩把一碗水推到我面前,“坐。”
我没动。
“那为什么,十年了,我才等到这句话?”
“因为魏忠。”苏文轩端起自己那碗水,吹了吹热气,“兵部尚书,国丈爷,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当年雁回关一战的军报、证词、人犯,全在他手里。陛下动不了他。”
“那你呢?”我盯着他,“苏侍郎家的公子,怎么搅进这浑水?”
苏文轩抬起眼。
烛光下,他眼底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父亲,苏明远。”他慢慢说,“当年是兵部侍郎,主管北境粮草调配。雁回关战败后三个月,他被查出‘贪墨军饷’,下狱,三个月后,病死狱中。”
我怔住。
苏明远。
我记得这个名字。雁回关战事最吃紧的时候,朝廷拨的粮草迟迟不到,我连发十二道急报。最后来的,只有一半,还是掺了沙的陈米。
副将沈云舟气得摔了碗。
“肯定是兵部那帮蠹虫中饱私囊!”
后来我才知道,押送粮草的军官,是魏忠的侄子。
“你父亲……”
“是被灭口的。”苏文轩放下碗,碗底磕在桌面上,一声轻响,“因为他发现了魏忠通敌的证据。”
屋里静下来。
灶膛里的火快熄了,只剩一点暗红的炭。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烛火乱晃,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抖。
“所以你这三年,”我听见自己问,“一直在查?”
“嗯。”
“查到什么?”
苏文轩从怀里摸出一个油布包,打开。
里面是几封信,纸已经发黄,边角磨损。他把信推到我面前。
“看看。”
我走过去,拿起最上面一封。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是北狄文字,我认得。当年在军中,我学过。
“腊月初七,雁回关左翼换防,守将为叶。可从此入。”
落款是一个印记:一只鹰,爪下抓着一把刀。
魏家的家徽。
我手指开始抖。
“这是……”
“魏忠与北狄二王子的通信。”苏文轩声音很冷,“一共七封。时间,从雁回关之战前半年,到战后三个月。内容,从关防部署,到粮草路线,到……战后如何清理‘知情者’。”
我一张一张看过去。
腊月十二,左军粮仓位置。
腊月十八,巡哨时间表。
腊月廿三,叶青梧每日巡查路线。
……
最后一张。
正月初三,雁回关大捷。叶青梧通敌,证据已备。沈云舟可接掌左军。
沈云舟。
我盯着那三个字,眼前发黑。
“沈云舟他……”喉咙像被什么堵住,后面的话说不出来。
“他不知道。”苏文轩说,“魏忠骗了他,说你是真通敌,那些证据都是真的。沈云舟信了,所以……”
所以那一箭,他射得毫不留情。
我闭了闭眼。
十年了。
我以为我已经忘了。
可那些画面,还是血淋淋地往脑子里钻。
那年冬天,特别冷。
雁回关外,雪积了三尺厚。北狄人像疯了一样攻城,一波接着一波。
我守左翼,沈云舟守右翼。
腊月廿九,夜里。
我正在军帐里看地图,亲兵冲进来,脸白得跟纸一样。
“将军!右翼、右翼被突破了!”
“什么?!”我扔了地图就往外冲。
刚出帐,就看见远处火光冲天。是粮仓。
紧接着,左翼后方也响起喊杀声。
中计了。
北狄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像早就知道我们的布防,专挑薄弱处打。
我带着亲卫队往右翼冲,想跟沈云舟汇合。
可到处都是敌人。
刀砍卷了刃,就抢敌人的。马被射死了,就步战。血糊了一脸,也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终于杀到右翼大营。
营门大开,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沈云舟一个人,站在校场中央。
他穿着甲,手里拿着弓,背对着我。
“沈云舟!”我喊他,“怎么回事?其他人呢?”
他慢慢转过身。
火光映着他的脸,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青梧。”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对不起。”
我没明白。
然后,他举起了弓。
箭尖对着我。
“你通敌。”他说,“证据确凿。陛下有旨,格杀勿论。”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雁回关布防图,是你卖给北狄的。”沈云舟手很稳,箭尖一动不动,“今夜偷袭路线,也是你泄露的。叶青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放屁!”我吼出来,“我叶家三代守边,我爹死在关外,我会通敌?!”
“可证据就在你帐中。”沈云舟闭了闭眼,“青梧,别让我为难。”
“我没有!”
话音未落,箭已离弦。
我本能地侧身,箭擦着脸颊飞过,带出一道血痕。
紧接着,第二箭,第三箭。
不是沈云舟一个人射的。
是埋伏在周围的弓箭手。
箭雨。
我拼命挥刀格挡,可箭太多了。左肩中了一箭,右腿中了一箭。
“撤!”我冲身后还活着的亲兵喊。
可来不及了。
四面八方都是人,穿着我们军的衣服,手里的刀却对着自己人。
是沈云舟的右翼军。
他们叛变了。
或者说,他们以为,叛变的是我。
“叶青梧通敌!杀叛徒者,赏金百两!”
不知道谁在喊。
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红着眼朝我冲过来。
我不能杀他们。
我只能退。
一路退,一路有人倒下。最后跟在我身边的,只剩三个亲兵。
我们逃进山里。
雪下得很大,脚印很快就被盖住。我肩上的箭没拔,每走一步都在淌血。
“将军,不行了。”一个亲兵喘着粗气,“您、您自己走……”
他话没说完,背后中箭,扑倒在雪地里。
剩下两个,一个替我挡箭死了,另一个拉着我跳下山崖。
崖下有河,冬天结了冰。
我们摔在冰面上,冰裂了,掉进水里。
刺骨的冷。
我拼命往上爬,可身上有甲,沉。那个亲兵把我推上冰面,自己却没上来。
“将军……活着……报仇……”
他沉下去了。
我趴在冰上,看着那个黑漆漆的窟窿,浑身抖得像筛糠。
后来,我不知道怎么爬上岸的。也不知道怎么拖着一条伤腿,走了三天三夜,走到柳叶村。
我昏死在村口的土地庙。
是王婶的男人,早起去镇上卖豆腐,发现了我。
他把我背回家,请了郎中。
郎中说,腿保住了,但会瘸。脸上的疤,去不掉了。
王婶问我是谁,从哪里来。
我说,我叫叶屠娘,家乡遭了灾,逃难来的。
她信了。
我在柳叶村住下来。用身上最后一点碎银,买了把杀猪刀,开始杀猪。
这一杀,就是十年。
“叶青梧。”
苏文轩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我睁开眼,脸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这些信,”我把那几张纸推回去,“你怎么拿到的?”
“魏忠有个心腹,叫周世荣。”苏文轩说,“现在是清河县县令。当年经手这些信的,就是他。三年前,他因为分赃不均,跟魏忠闹翻了,偷偷留了副本,想保命。”
“人呢?”
“死了。”苏文轩淡淡道,“两个月前,‘失足’落水。他儿子周玉娇,现在在县令府,把这些信当保命符藏着。”
周玉娇。
我想起来了。
是县令家那个小姐。上个月来柳叶村上香,路上轿子坏了,在我这儿歇过脚。娇滴滴的,嫌我院子里有猪粪味儿,拿帕子捂了半天鼻子。
“你来找我,”我看着苏文轩,“不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吧?”
苏文轩笑了。
这是今晚,他第一次笑。
“夫人聪慧。”他说,“我要借你的刀,杀几个人。”
“谁?”
“第一个,周世荣。不过他已经死了,便宜他了。”苏文轩手指在桌上点了点,“第二个,贾富贵。”
我挑眉。
“他?一个地主,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
“他是周世荣的白手套。”苏文轩说,“当年雁回关粮草被贪,其中三成,经周世荣的手,流进了贾富贵的粮铺。这十年,他靠那笔钱发家,成了柳叶村一霸。”
“还有呢?”
“第三个,”苏文轩顿了顿,“沈云舟。”
我手指猛地蜷紧。
“他……”
“他现在是北境军主将,魏忠的女婿。”苏文轩看着我,“三年前娶了魏忠的侄女。雁回关之后,他接掌左军,三年内连升三级。如今,是正三品怀化将军。”
我沉默了。
怪不得。
怪不得他当年会信那些“证据”。
怪不得他会对我放箭。
原来,早就选好了路。
“你要我怎么做?”我问。
“等。”苏文轩说,“周玉娇藏的那些信,我已经派人去取了。最迟三天,会有消息。到时候,贾富贵会第一个倒霉。我们需要一个人,把他逼急,让他去动那些信。”
“谁?”
“他儿子,贾仁。”苏文轩笑了笑,“贾富贵老来得子,宠得跟眼珠子似的。可惜,是个赌鬼。在县城赌坊欠了一屁股债,明天,债主就该上门了。”
我明白了。
“你是要我去‘救’贾仁?”
“对。”苏文轩说,“你杀猪,力气大,能打。贾富贵肯定会来求你。你答应,但要他拿粮铺的地契作抵押。他拿不出,就会去动那些信。到时候,我们人赃并获。”
“然后呢?”
“然后,顺藤摸瓜,揪出魏忠。”苏文轩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叶将军,你想报仇吗?”
我没说话。
报仇。
我想了十年。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次拿起杀猪刀,我都想。
可我更想知道——
“沈云舟,”我低声问,“他知道真相吗?这些年,他知道自己当年杀错人了吗?”
苏文轩转过身。
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他知道。”他说,“两年前,他就知道了。我托人给他捎过信,把证据的副本,送了一份给他。”
“他什么反应?”
“没反应。”苏文轩声音很冷,“他烧了信,杀了送信的人。然后,给他岳父魏忠,写了封密报,说我在查旧案。”
我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
“所以……”
“所以魏忠才会派人来柳叶村。”苏文轩走回桌边,拿起那碗已经凉透的水,一饮而尽,“叶青梧,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配得到原谅。”
雪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推开院门的时候,雪停了。
屋檐下挂着的猪排骨冻得硬邦邦的。我取下来,拎到后院,开始剔骨。
刀锋划过骨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
苏文轩从西屋出来,换了身半旧的棉袍,手里拿着本书,坐在檐下的小凳上看。
像真的只是个穷教书先生。
“今天还去学堂?”我问。
“嗯。”他头也不抬,“那几个娃娃,快学完《千字文》了。”
我没再说话,专心剔肉。
快到晌午的时候,前院传来哭喊声。
是贾富贵。
他连滚带爬冲进来,扑通就给我跪下了。
“屠娘!叶屠娘!救命啊!”
我放下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怎么了?”
“仁儿、仁儿被县城赌坊的人扣了!”贾富贵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说要一百两!不给就剁手!我、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哦。
戏开场了。
“我也没有。”我说。
“你有!你有!”贾富贵抱住我的腿,“苏先生!苏先生是读书人,肯定有办法!屠娘,我求求你,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我看向苏文轩。
他放下书,叹了口气。
“贾老爷,不是我不帮。一百两,实在太多了。”
“那、那怎么办……”贾富贵瘫在地上,面如死灰。
苏文轩沉吟片刻。
“我倒是有个主意。县城赌坊的东家,我认得。可以替你求个情,宽限几日。但需要抵押。”
“抵押!什么都行!”贾富贵眼睛亮了,“我家的地!铺子!都行!”
“地契铺契,可都值钱。”苏文轩慢条斯理,“就怕赌坊的人看不上。我倒听说,贾老爷手里,有些别的‘东西’,比地契更值钱?”
贾富贵脸色变了。
“你、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周县令生前,是不是托你保管过一些‘信’?”苏文轩俯身,声音压低,“用那些信,换你儿子一条命。如何?”
贾富贵浑身一抖。
“你、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不重要。”苏文轩直起身,“重要的是,你儿子的一只手,和那些信,你选哪个。”
贾富贵瘫在地上,像条离水的鱼,大口喘气。
过了很久,他哑着嗓子说。
“信……在我家祠堂,祖宗牌位后面的暗格里。”
苏文轩笑了。
“很好。”
他冲我点了点头。
我拎起剔骨刀,往外走。
“去哪儿?”贾富贵问。
“救你儿子。”我说。
县城,如意赌坊。
我拎着刀进去的时候,赌坊里正热闹。乌烟瘴气,一群汉子围着桌子,脸红脖子粗地喊“大大大”“小小小”。
贾仁被绑在柱子上,鼻青脸肿。旁边站着两个打手,手里拿着棍子。
“爹!爹救我!”贾仁看见我,愣了下,“怎么是你?我爹呢?”
“你爹在家筹钱。”我把刀往地上一拄,“人我带走,钱三天后送来。”
打手们哄笑。
“你谁啊?一个娘们,拎把杀猪刀,吓唬谁呢?”
“就是!一百两,少一个子儿,这小白脸的手就别要了!”
我往前走了一步。
“我说,人我带走。”
“哟呵,还挺横——”一个打手抡着棍子朝我砸过来。
我没躲。
抬手,用刀背一挡。
棍子断了。
打手愣住了。
我反手,刀背拍在他脸上。
他惨叫一声,飞出去,砸翻了一张赌桌。
骰子、筹码、碎银子,哗啦啦撒了一地。
赌坊里静了一瞬。
然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抄家伙!”不知谁喊了一声。
我握紧刀。
十年了。
十年没跟人动过手了。
不知道这把杀猪刀,还利不利。
第三章 血刃与昭雪
刀背砸在第一个冲上来的打手手腕上。
咔嚓一声,骨头断了。
那人惨叫都没喊全,就被我一脚踹飞,撞倒了后面三四个。
赌坊里乱成一团。
“抄家伙!弄死她!”
七八个打手抄起棍子、板凳,围上来。我往后退了半步,背靠柱子,侧身躲过砸来的板凳,手里的杀猪刀横着一扫。
刀锋没开刃,是钝的。
但力道够大。
砸在腿上,能断腿。砸在胳膊上,能脱臼。
这是杀猪十年的经验——想让猪老实挨宰,得先让它疼,疼到没力气挣扎。
用在人身上,也一样。
不到半盏茶工夫,地上躺了一片。断腿的抱着腿嚎,断胳膊的蜷成虾米,还有个脑门挨了一下,翻着白眼吐白沫。
赌坊管事从后院冲出来,看见这场面,脸都绿了。
“你、你是什么人?!”
“叶屠娘。”我把刀往地上一拄,血珠顺着刀身往下滴,“贾仁我带走了。钱,三天后,贾富贵送来。”
“你敢——”管事话没说完,我往前一步,刀尖指着他鼻子。
“要么放人,要么,我拆了你这赌坊。”
管事哆嗦着,往后退。
“放、放人!”
打手们七手八脚把贾仁从柱子上解下来。贾仁腿软得站不住,我拎着他后领,拖出赌坊。
外头太阳正好,街上人来人往。
看见我拎着个鼻青脸肿的男人出来,手里还拎着把滴血的刀,所有人都往两边躲。
我当没看见,拖着贾仁往城门口走。
“谢、谢谢屠娘……”贾仁结结巴巴。
“闭嘴。”
我把他扔上驴车——来的时候租的,回去还得靠它。
赶车的老汉看见我这一身血,脸都白了。
“姑、姑娘……”
“回柳叶村。”我扔给他几个铜板,“快点。”
驴车吱吱呀呀出了城。
贾仁缩在车角,大气不敢出。
我靠着车板,看着路边的树往后倒。手里还握着刀,刀上的血慢慢凝了,变成暗红色的痂。
十年了。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碰这些。
可刚才,那些人围上来的时候,身体自己就动了。
像十年前在雁回关。
像无数次在战场上。
原来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头里的。杀猪十年,也洗不掉。
回到柳叶村,天已经擦黑。
我把贾仁扔在贾家门口,没进去。贾富贵扑出来抱着儿子哭,我没理,径直回家。
院里,苏文轩在喂鸡。
听见动静,他抬头看我一眼。
“解决了?”
“嗯。”
“没伤人吧?”
“断了几个手脚,死不了。”
他点点头,继续撒米。
我走到井边,打水洗手。水冰凉,冲掉手上的血污,露出几道新添的擦伤。
“信拿到了吗?”我问。
“拿到了。”苏文轩放下簸箕,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扔给我。
我打开。
里面是几封信,纸很新,墨迹也新。不是当年那些。
“假的?”
“真的在县令府。”苏文轩说,“周玉娇藏得严实,我的人还没找到。这些是我仿的,但足够让贾富贵相信。”
“然后呢?”
“然后,等鱼上钩。”
苏文轩说的鱼,第二天就来了。
是个生面孔,穿着绸缎衣裳,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四个随从,直奔贾家。
村里人都跑出来看热闹。
“谁啊?排场这么大。”
“像是县城来的……”
“贾富贵攀上高枝了?”
我也站在院门口看。
那人进了贾家,不到一炷香工夫就出来了。贾富贵跟在后面,点头哈腰,脸笑得像朵菊花。
等人走了,贾富贵看见我,愣了一下,转身想溜。
“贾老爷。”我喊住他。
他僵着脖子转过来。
“屠、屠娘……”
“钱,什么时候还?”我问。
“还、还什么钱?”
“赌坊那一百两。”我往前走一步,“我替你儿子挨的打,你忘了?”
贾富贵脸白了。
“我、我没钱……”
“没钱?”我看了眼那绸缎男人离开的方向,“刚才那位,不是给你送钱来的?”
“那是、那是……”贾富贵支支吾吾。
“是买信的吧。”苏文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手里拿着本书,靠在门框上,慢悠悠地说。
贾富贵脸色大变。
“你、你胡说什么!”
“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苏文轩笑了笑,“周县令留下的那些信,你卖给刚才那位,得了多少?五百两?一千两?”
贾富贵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你、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买信的人,是魏忠派来的。”苏文轩走过来,声音压低,“贾老爷,你胆子不小啊。魏忠的东西,你也敢卖?”
“我、我没卖!”贾富贵慌了,“是、是借!借给他们看看!”
“借?”苏文轩挑眉,“那他们什么时候还?”
贾富贵答不上来。
苏文轩也不逼他,转身回院。
“贾老爷,好自为之。那些信要是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别说你儿子,你全家,都保不住。”
贾富贵呆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冲过来,扑通跪在我面前。
“屠娘!叶屠娘!你救救我!苏先生、苏先生一定有办法!你帮我说说话!”
我低头看着他。
“我凭什么帮你?”
“我、我把地契给你!”贾富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粮铺的!还有我家的田!都给你!你让苏先生救救我!”
我接过地契,看了看。
是真的。
“那些信,你从哪儿拿的?”我问。
“就、就祠堂牌位后面……”贾富贵哭丧着脸,“可刚才那人说,那是假的!真的还在县令府!他们让我去偷,偷不到,就要我的命!”
哦。
所以魏忠的人,也没拿到真的。
信还在周玉娇手里。
“你想让我帮你偷信?”我问。
“不、不是偷!”贾富贵爬起来,凑近,压低声音,“是换!周小姐不知道那些信是假的,你拿假的,跟她换真的!等魏大人的人再来,我把真的给他们,就没事了!”
我看着他。
这个人,贪了不该贪的钱,卖了不该卖的信,现在知道怕了。
可惜,晚了。
“行。”我说,“我去换。”
贾富贵千恩万谢地走了。
我捏着地契,回屋。
苏文轩在桌边喝茶。
“答应了?”
“嗯。”
“今晚?”
“嗯。”
苏文轩放下茶杯。
“我跟你去。”
夜里,二更天。
县令府后墙。
我换了一身黑衣,蒙着脸。苏文轩也换了黑衣,但他那身板,怎么看都不像能翻墙的。
“你在外头等着。”我说。
“我会功夫。”他挑眉。
“会功夫,和能翻墙,是两回事。”我指了指墙头,“这墙一丈高,你上得去?”
苏文轩不说话了。
我退后几步,助跑,蹬墙,手扒住墙头,一撑,翻了过去。
落地无声。
墙那边是个小花园,黑漆漆的,没人。我摸到后门,开了门闩,让苏文轩进来。
“周玉娇住西厢。”他低声说,“我白天来踩过点。”
我们摸到西厢。
窗纸透着光,里面有人影晃动。是个丫鬟,在铺床。
等丫鬟出去,灯灭了,我才撬开窗户,跳进去。
苏文轩跟在后面,动作居然不慢。
屋里很香,是那种甜腻的脂粉味儿。我屏住呼吸,摸到梳妆台,开始翻。
首饰盒,没有。
衣柜,没有。
床底下,没有。
“会在哪儿?”我皱眉。
苏文轩走到书架前,一本一本摸过去。摸到第三排,停住,抽出一本《女诫》。
书页中间是挖空的,里面放着一个油布包。
他打开,看了一眼,点头。
是真的。
我把怀里假的塞进去,书放回原处。
正要走,外头传来脚步声。
“小姐,您慢点……”
是周玉娇的声音。
“滚开!不用你扶!”
门被推开。
我和苏文轩躲在衣柜后面,屏住呼吸。
周玉娇摇摇晃晃走进来,一身酒气。她走到梳妆台前,坐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笑起来。
“爹……你看见了吗……女儿要嫁进魏家了……”
她笑着笑着,又哭了。
“可那些信……那些信怎么办……魏大人要是知道,信是爹偷留的……会不会杀了我……”
她趴在桌上,呜呜地哭。
哭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摇摇晃晃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女诫》。
打开,拿出油布包。
“得烧了……”她喃喃道,“烧了就干净了……”
她摸出火折子,吹亮。
火光映着她的脸,狰狞又脆弱。
就在她要烧信的瞬间,苏文轩动了。
他像道影子,窜出去,一把夺过油布包,同时一掌劈在周玉娇后颈。
周玉娇软软倒下。
“走。”苏文轩说。
我们原路返回,翻出后墙。
刚落地,就听见县令府里响起锣声。
“有贼!抓贼啊!”
“快!去西厢!”
我们沿着巷子狂奔。
身后传来脚步声,还有狗叫声。
“分开跑!”我说,“老地方见!”
苏文轩点头,拐进另一条巷子。
我继续往前,跑过两条街,翻进一户人家的后院,躲进柴堆。
狗叫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
“在那边!追!”
“别让他跑了!”
我蜷在柴堆里,手里握着刀。
十年了。
十年没这么跑过。
心跳得像要炸开,肺里火烧火燎。
可奇怪的是,我不害怕。
甚至有点……兴奋。
像当年在战场上,带着小队偷袭敌营。
脚步声越来越近。
“搜!一家一家搜!”
柴堆被扒开。
火光刺眼。
我握紧刀,准备冲出去。
“住手。”
一个声音响起。
低沉,沙哑,带着久经沙场的铁血味。
我浑身一僵。
这个声音,我死都记得。
沈云舟。
柴堆被彻底扒开。
火光里,站着一个人。
穿着玄色劲装,外罩暗红披风,腰佩长剑。脸在阴影里,看不真切,可那身形,那轮廓,我闭着眼都能认出来。
沈云舟。
十年了。
他好像没怎么变。还是那么高,那么挺,像棵松。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下巴上有了青茬。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是你。”他说。
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没说话,慢慢站起来,手里还握着刀。
“将军……”他身后的副将想说什么,被他抬手止住。
“都退下。”他说。
“可是——”
“退下。”
副将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退到巷子外。
柴院里只剩我们两个人。
沈云舟往前走了一步。
火光跳了一下,照亮他的脸。
他老了。
我也老了。
“我以为你死了。”他说。
“让你失望了。”我说。
他笑了笑,那笑容有点苦。
“这些年,过得好吗?”
“好。”我说,“杀猪,卖肉,还债。挺好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当年……”
“当年你给了我一箭。”我打断他,“差点要了我的命。”
“是。”他承认得很干脆,“那一箭,是我射的。”
“为什么?”
“军令。”他说,“军令如山。”
“谁的命令?”
“魏忠。”
哦。
果然。
“你知道我是冤枉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两年前,有人给你送过信。”
沈云舟脸色变了。
“你……怎么知道?”
“信是我让人送的。”我说。
他瞳孔猛地一缩。
“叶青梧——”
“苏砚,苏文轩,我丈夫。”我说,“他在查当年的案子。那些信,是他从周世荣那儿拿到的。你也有一份,对吧?”
沈云舟没说话。
但他的手,握紧了剑柄。
“你烧了信,杀了送信的人,然后给魏忠报信,说有人在查旧案。”我一字一句,“沈云舟,你他妈就是个孬种。”
“我没有选择。”他声音发紧,“魏忠是我岳父,我妻子是他侄女,我全家都在京城——”
“所以你就看着我死?”我往前走一步,刀尖对着他,“看着我三万兄弟死在雁回关?看着我爹一世英名被污成叛贼?沈云舟,当年在军中,你说过什么?你说,将军在,云舟在,北境在。你说,这辈子,绝不负我。”
我笑了,笑出了眼泪。
“结果呢?一箭,差点要了我的命。十年,不闻不问。沈云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沈云舟的脸,在火光下白得吓人。
“对不起。”他说。
“对不起有屁用。”我抹了把脸,“那些信,在我这儿。你要抢,就来。要么杀了我,要么,我拿这些信,去京城,告御状。”
“你告不倒魏忠。”沈云舟声音发涩,“他在朝中经营二十年,门生故旧遍布——”
“那就不告。”我说,“我杀了他。”
沈云舟怔住。
“你说什么?”
“我说,我杀了他。”我盯着他,“用这把杀猪刀。一刀,一刀,把他剁了喂狗。”
“你疯了。”
“我是疯了。”我笑,“从你对我放箭那天起,我就疯了。”
沈云舟闭上眼睛。
过了很久,他睁开。
“信给我。”他说,“我保你平安离开清河县。这辈子,别再回来。”
“然后呢?让你拿着信,继续给魏忠当狗?”
“叶青梧!”他低吼,“你别逼我!”
“是你逼我。”我说。
我们僵持着。
巷子外传来马蹄声。
是苏文轩。
他骑马冲进来,身后跟着一队兵——不是魏忠的人,穿着另一身甲胄,是我没见过的样式。
“走!”他朝我伸手。
我没动。
“他是谁?”沈云舟盯着苏文轩。
“我丈夫。”我说。
沈云舟脸色更难看了。
苏文轩骑马到近前,居高临下看着沈云舟。
“沈将军,别来无恙。”
“苏砚。”沈云舟咬牙,“果然是你。”
“是我。”苏文轩笑了笑,“怎么,沈将军要在这里杀了我?可以啊,动手。不过提醒你一句,我带来的,是陛下亲卫。杀我,就是谋反。”
沈云舟的手,松开了剑柄。
“你们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苏文轩跳下马,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带夫人回家。至于魏忠——”
他看向沈云舟,笑容冷了。
“沈将军,给你两个选择。一,跟我们一起,扳倒魏忠,将功补过。二,继续给他当狗,然后,跟他一起死。”
沈云舟没说话。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
“将军!”副将追上来。
“撤。”沈云舟说。
“可是——”
“我说,撤。”
马蹄声渐远。
苏文轩松开我的手。
“没事吧?”
“没事。”我说,“信呢?”
“在这儿。”他掏出油布包,“走吧,先回家。”
回到柳叶村,天快亮了。
我们把信摊在桌上,一封一封看。
除了之前那些,还有几封新的。是魏忠跟北狄二王子的密信,时间就在最近。
“他们在谋划什么?”我问。
“开春,北狄会再次南下。”苏文轩指着地图,“这次,他们会绕过雁回关,从西边的落霞谷进来。魏忠会故意放水,让他们连破三城,直逼京城。”
“然后呢?”
“然后,陛下被迫御驾亲征。魏忠会在战场上‘救驾’,立下大功,趁机逼宫,扶他外孙——也就是现在的太子——登基。”
我倒吸一口凉气。
“太子才八岁。”
“所以,魏忠会摄政。”苏文轩敲了敲桌子,“到那时,大权在握,他想杀谁,就杀谁。”
“包括你和我。”
“包括所有知道他秘密的人。”
窗外,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鸡叫了。
“我们怎么办?”我问。
“进京。”苏文轩说,“把这些信,亲手交给陛下。”
“沈云舟不会让我们活着到京城。”
“所以,我们得快。”苏文轩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天亮就走,骑马,日夜兼程,七天应该能到。”
“贾富贵呢?”我问。
“他已经没用了。”苏文轩顿了顿,“魏忠的人不会放过他。不过,他儿子贾仁,我们可以带上。”
“带他干什么?”
“他是人证。”苏文轩说,“当年粮草贪墨的事,他爹经手,他知道内情。”
我点头。
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一些干粮。苏文轩去牵马——他早就准备好了,两匹好马,藏在村外林子里。
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土坯房。
住了十年。
养猪,杀猪,卖肉。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没想到,还是要走。
“走吧。”苏文轩说。
我们翻身上马,往村外奔去。
路过王婶家,我勒住马,从怀里掏出一袋碎银子,扔进她家院子。
算是谢她十年照顾。
马出村口的时候,天亮了。
雪停了,太阳出来,照在雪地上,刺眼。
我回头看了一眼柳叶村。
小小的,静静的,像幅画。
然后,我转身,策马。
“驾!”
马飞奔起来。
风刮在脸上,像刀。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
十年了。
叶青梧,该回去了。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