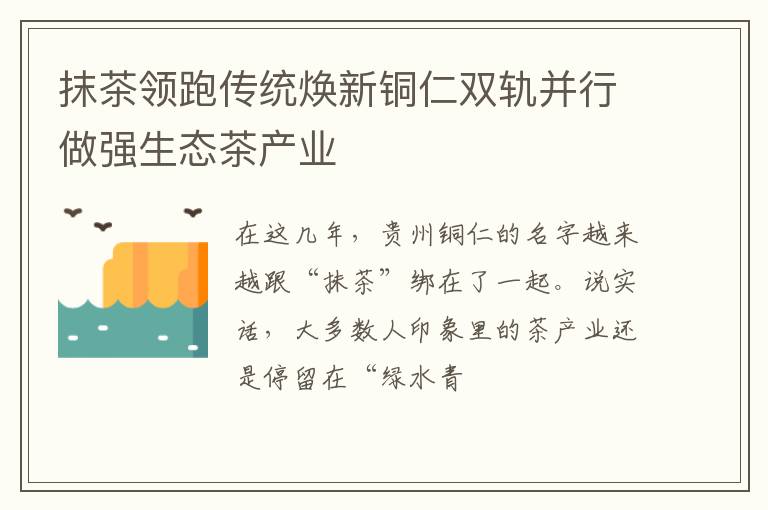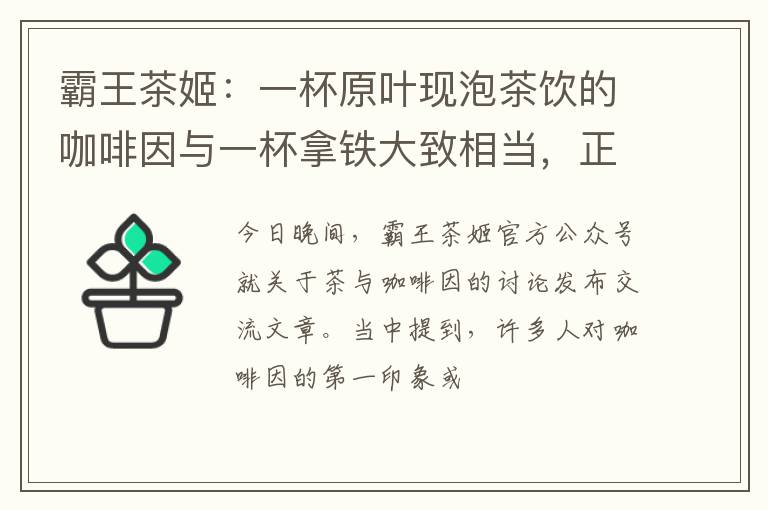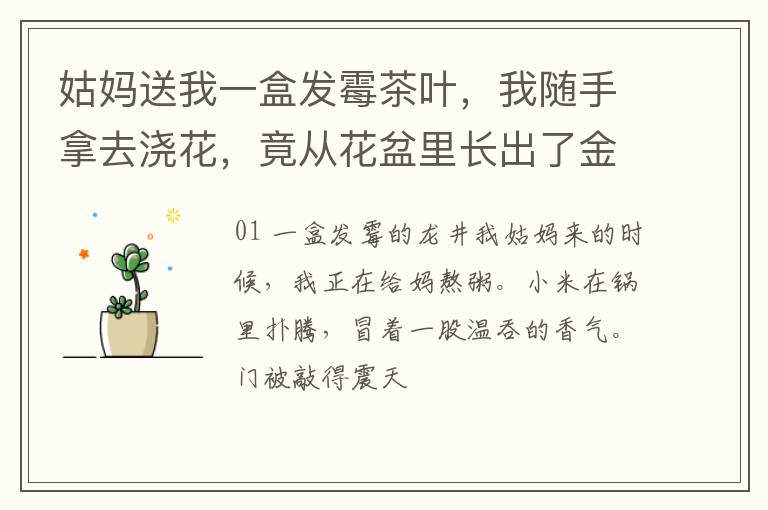
01 一盒发霉的龙井
我姑妈来的时候,我正在给妈熬粥。
小米在锅里扑腾,冒着一股温吞的香气。
门被敲得震天响,梆梆梆,像是来讨债的。
我赶紧关了小火,跑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果然是她,我妈的亲姐姐,程筝。
她烫着一头棕色的小卷毛,穿着一件紧身的花衬衫,手臂上挎着一个菜篮子。
“佳禾啊,开个门比蜗牛还慢。”
她一边说,一边已经挤了进来,自顾自换了拖鞋。
那双拖鞋是我特意给她备的,她嫌弃小区超市的便宜货硌脚,非要我买了双带按摩底的。
“姑妈,您怎么来了。”
我接过她手里的菜篮,里面空空如也。
“我来看看你妈,顺便给你送点好东西。”
她说着,从自己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包装精美的铁盒子,往我餐桌上“啪”地一放。
“喏,上好的明前龙井,别人送我的,我一口没喝,特地拿来给你尝尝。”
那盒子确实漂亮,淡绿色的底,上面印着水墨山水。
我心里掠过一丝暖意。
我妈生病以来,花钱如流水,我已经很久没买过超过五十块一斤的茶叶了。
“谢谢姑妈。”
我真心实意地说。
“跟我客气什么。”
她摆摆手,眼睛却在我这间租来的小两居里滴溜溜地转。
“你妈呢?”
“在房间里躺着呢,医生说要多休息。”
“啧,这病就是娇贵。”
她撇撇嘴,踱步到我妈的房门口,象征性地朝里面望了一眼。
“姐,你来了。”
我妈虚弱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嗯,来了。你好好躺着吧,我跟佳禾说几句话。”
姑妈说完,就把房门轻轻带上了。
她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
“佳禾,你妈那个进口药,是不是又要交钱了?”
我的心沉了一下。
“嗯,下周又要交一个季度的。”
“多少钱?”
“三万二。”
我报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嗓子眼都发紧。
“这么多?”
姑妈的调门一下子高了八度,随即又压了下去,生怕被我妈听见。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知道想想法子呢?”
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我在想了,姑妈。”
“你想?你能想出什么法子?你那点死工资,还不够给你妈塞牙缝的。”
她戳了戳我的脑门。
“我跟你说,你表弟,承川,他那个朋友,最近在做一个什么项目,听说特别赚钱。”
我心里“咯噔”一下。
陆承川,我那个眼高于顶的表弟,从小就被姑妈宠得不知天高地厚。
他嘴里的“赚钱项目”,十个有九个是坑。
“姑妈,那些东西不靠谱……”
“你懂什么!”
她打断我,“人家现在都开上宝马了!我是看你可怜,想拉你一把。”
“你手里还有多少钱?凑个五万块,让你表弟带带你,不出半年,你妈的药钱就全回来了。”
我沉默了。
我手里所有的积蓄,加上跟朋友借的,凑起来也就两万出头,那是给我妈留的救命钱。
“姑"妈,我没钱。”
我低着头说。
“没钱?”
姑妈的眼睛立刻瞪圆了,“你上班这么多年,一分钱没存下?你是不是都乱花了?”
“我妈看病……”
“行了行了,知道了。”
她不耐烦地挥挥手,“指望不上你。对了,我那把备用钥匙你放哪儿了?我上次来好像没找到。”
多年前,她以“方便过来照顾你们母女”为由,硬是去配了一把我家的钥匙。
“在玄关的抽屉里。”
我平静地说。
她走过去,拉开抽屉翻了翻,确认钥匙还在,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行了,粥是不是要糊了?我先走了,公司还有事。”
她拿起她的名牌包,看都没看那盒茶叶一眼,踩着她的高跟鞋哒哒哒地走了。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走到灶台边,关了火。
粥还好,只是有点稠了。
我盛了一碗,吹了吹,端进我妈的房间。
我妈靠在床头,脸色蜡黄。
“你姑妈……又跟你说承川那个事了?”
“嗯。”
“别听她的。咱有多少钱,就治多少病,别去碰那些歪门邪道。”
我妈拉着我的手,她的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知道的,妈。”
我喂她喝完粥,收拾了碗筷,回到客厅。
那盒孤零零的茶叶还摆在桌上。
我坐下来,端详了许久,还是决定打开它。
或许,一杯好茶,能冲淡一些心里的苦涩。
铁盒的盖子有点紧,我费了点劲才撬开。
一股奇异的味道扑面而来。
不是茶香。
是霉味。
一种混合着陈腐和潮湿的,让人很不舒服的味道。
我愣住了。
盒子里,所谓的“明前龙井”,已经结成了一块一块的墨绿色茶饼。
上面甚至还长出了一些白色的、毛茸茸的菌丝。
我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茶饼就碎了,散发出的霉味更浓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这盒发霉的茶叶,许久没有动。
心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比窗外的冬夜还冷。
桌上的手机亮了一下,是表弟陆承川发来的朋友圈。
一张九宫格照片,全是他那辆新提的二手宝马,配文是:“感谢妈妈赞助的三十万,以后你儿子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了。”
我忽然就笑了。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拿起那盒茶叶,走到阳台。
楼下是城市的车水马龙,闪烁的霓虹灯显得那么不真实。
我不想把它就这么扔进垃圾桶。
太便宜它了。
我看着墙角那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那是我妈住院前最宝贝的,现在被我养得叶子都黄了。
鬼使神差地,我把那盒发霉的茶叶,一点一点,全都倒进了君子兰的花盆里。
就当是给它最后的肥料吧。
做完这一切,我拍了拍手上的茶末,转身回了屋。
那一刻,我没指望任何事发生。
02 金芽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闹钟叫醒的。
给公司请了假,我得带我妈去做复查。
我习惯性地走到阳台,想拉开窗帘透透气。
就是这一眼,我愣住了。
墙角那盆君子兰,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原本耷拉着的几片黄叶子,竟然挺拔了一些。
更奇怪的是,在几片宽大的绿叶之间,我好像看到了……一点金色的反光。
我以为是自己没睡醒,眼花了。
我走过去,蹲下身,凑近了看。
不是幻觉。
就在君子兰最中心的位置,那原本应该长出新叶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嫩芽。
一个通体金黄的嫩芽。
它只有小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形状和君子兰的新芽很像,但颜色却是纯粹的、灿烂的金色。
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着一层柔和又坚实的光。
我伸出手,想去摸一下,指尖却在离它一厘米的地方停住了。
我怕它是个梦,一碰就碎了。
这是什么?
难道是那盒发霉的茶叶?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荒唐。
茶叶浇花,顶多就是个肥料,怎么可能长出金子做的芽?
肯定是某种真菌,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的植物病变。
我拍了拍自己的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今天还要带我妈去医院,不能耽误了正事。
我匆匆洗漱,做了简单的早饭,然后扶着我妈出了门。
医院里人山人海,挂号,排队,检查。
一整个上午,我都在各种窗口和科室之间奔波。
我妈的检查结果不太好,医生建议,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还是用之前提到的那种进口药,虽然贵,但是副作用小,效果也更明确。
我握着缴费单,看着上面那个“32000”的数字,感觉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口。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下午。
我妈大概是累了,在出租车上就睡着了。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脑子里却反反复复地出现那个金色的嫩芽。
万一……
万一呢?
这个念头就像一根疯狂生长的藤蔓,缠得我喘不过气。
回到家,安顿好我妈,我第一件事就是冲向阳台。
那个金色的嫩芽,还在。
而且,它好像比早上我看到的时候,又长大了一点点。
现在已经有我的半个小拇指那么大了。
颜色也更深了,是一种沉甸甸的,赤金的颜色。
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
我找来一把小镊子和一把指甲刀,手抖得厉害。
我决定,要把它弄下来一点,去验证一下。
我深吸一口气,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住金芽的顶端,然后用指甲刀,轻轻地,剪下了一小片。
大概只有米粒那么大。
剪下来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都停跳了。
那金色的碎片掉在我的手心,沉甸甸的,带着一种金属特有的冰凉触感。
我把它用纸巾小心翼翼地包好,揣进口袋,感觉那个口袋像着了火一样烫。
我跟我妈说我出去买点东西,然后飞快地跑下了楼。
我们小区附近就有一家老字号的金店。
我站在金店门口,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敢走进去。
店里的伙计看我穿得普普通通,神色紧张,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
“你好,我想……验个东西。”
我把那个纸包打开,把那粒金色的碎屑倒在柜台的绒布上。
伙计愣了一下,随即拿起一个小镊子夹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
“小姐,你这个……是哪儿来的?”
“您先别管是哪儿来的,能帮我看看,是金子吗?”
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他没说话,把它放进一个专业的小仪器里。
仪器发出一阵轻微的蜂鸣声。
几秒钟后,伙计抬起头,眼神彻底变了。
从审视,变成了震惊。
“小姐,”他咽了口唾沫,“这是……千足金,纯度非常高。”
轰的一声。
我感觉我脑子里所有的弦都断了。
是真的。
竟然是真的金子。
我家的花盆里,真的长出了金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金店的。
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痛。
我靠在墙上,感觉天旋地转。
发财了。
我竟然,用一盒发霉的茶叶,种出了金子。
我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摊开手心,看着那粒被还回来的金色碎屑。
它那么小,却又那么重。
重得像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
冷静。
阮佳禾,你必须冷静。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尤其是,不能让我姑妈知道。
我走到阳台,看着那盆君子兰,它现在在我的眼里,已经不是一盆花了。
它是一个秘密。
一个能改变我和我妈命运的,天大的秘密。
我看着那个被我剪掉一小块的金芽,它的“伤口”处,竟然又开始泛起了一点点金色的光晕,像是在自我修复。
它还在长。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为了防止我妈一个人在家出意外,也为了能随时看看她,我之前在客厅装过一个很小的家用监控。
但是阳台是死角,拍不到。
不行。
我必须得看着它。
我立刻打开手机,在网上下单了一个最小型号的针孔摄像头,选了最快的同城闪送。
我要把它装在阳台最隐蔽的角落,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这盆花。
我不能允许它出任何一点差错。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03 第一根金条
摄像头很快就装好了。
我把它藏在一个空花盆的排水孔里,镜头正对着那盆君子兰,角度刁钻又隐蔽。
从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就多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观察那根金芽的生长。
它长得比我想象中要快。
第二天,它就完全修复了被我剪掉的缺口。
第三天,它已经从小拇指大小,长到了食指那么长。
它不再是“芽”了,而是一根细细的、金灿灿的……条。
它的形状很奇特,不像自然生长的植物,反而像一根被精心打磨过的、不规则的金条,只是根部还连接着君子兰的茎。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我妈或者突然上门的姑妈发现这个秘密。
我把那盆君去子兰搬到了阳台最角落的位置,还用另外几盆高大的绿植挡在它前面,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
一个星期后,那根金条长到了大概十厘米长,有我大拇指那么粗。
它不再继续生长了,根部与植物连接的地方,颜色开始变浅,好像养分供给不足了。
我有一种预感,它可以“收获”了。
那天晚上,我等我妈睡熟了,蹑手蹑脚地溜到阳台。
我用一把消过毒的手术刀,屏住呼吸,在那根金条和君子兰的连接处,轻轻一划。
它应声而落。
我用一块提前准备好的绒布接住了它。
沉甸甸的。
我把它拿到台灯下,那光芒几乎晃花了我的眼。
我用厨房的电子秤称了一下。
125.6克。
按照现在的金价,这根金条,价值超过六万块。
我妈一个季度的药钱,还绰绰有余。
我抱着那根冰凉的金条,坐在地上,哭了。
不是伤心,是激动,是委屈,是终于看到希望的释放。
第二天,我找了个借口,带着身份证和金条,去了一家离家很远的、从没去过的黄金回收店。
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把它切割成了好几块。
店主检验过后,什么都没问,爽快地给我转了账。
看着手机银行里多出来的六万多块钱,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我没有立刻去交钱。
我先去商场,给自己换了一部最新款的手机。
我的旧手机已经卡得不行了,摄像头也花了,连给我妈拍张清晰的照片都做不到。
然后,我给我妈买了很多她以前爱吃、但因为贵而舍不得买的水果和营养品。
最后,我才去了医院,一次性交了半年的药费。
当我把缴费单拿给我妈看的时候,她愣住了。
“佳禾,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又跟我们总监借了点。”
我早就想好了说辞。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人情债最难还了。”
我妈心疼地直掉眼泪。
“妈,没事,只要您能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我抱着她,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以为日子会就这么平静地好起来。
我错了。
麻烦,是闻着钱味儿来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给我妈炖汤,门又被敲响了。
还是那种熟悉的、急促的节奏。
我心里一紧,打开门,果然又是姑妈程筝。
她今天穿得更“贵气”了,脖子上戴着一串饱满的珍珠项链。
“哟,佳禾在家呢?”
她笑眯眯地走进来,眼睛却第一时间落在了我放在玄关柜上的新手机上。
“换手机了?最新款的吧?得一万多?”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味。
“嗯,旧的坏了。”
我淡淡地回答。
“啧啧,你这孩子,就是大方。你妈看病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一个手机而已,能用不就行了。”
她嘴上说着教训的话,眼睛却没离开那部手机。
“对了,你上次说,你妈的药费要三万多,交了吗?”
她状似不经意地问。
“交了。”
“交了?”
她音调又高了,“你哪来的钱?你不是说你没钱吗?”
“我跟我们领导借的。”
我重复着对付我妈的说辞。
“借的?”
姑妈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你们什么领导这么好心,肯借给你这么多钱?男的女的?多大年纪了?没对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吧?”
她一连串的问题,像机关枪一样。
“姑妈,您想多了,我们领导是个快退休的女总监,人很好。”
“哼,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冷哼一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就啃。
那是我刚买的进口蛇果。
“这苹果不错,挺甜的。在哪儿买的?不便宜吧?”
“还好。”
“佳禾啊,”她话锋一转,突然凑近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发财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姑妈,您说什么呢,我发什么财。”
“你别骗我了。”
她指了指我的手机,又指了指桌上的水果,“你这消费水平,可不像是一个要给你妈凑医药费的人。”
“是不是买了什么彩票?还是……你背着我们,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她的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仿佛要看穿我的一切。
“没有,您真的想多了。”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转身去厨房看我的汤。
“我就是觉得,不能在吃穿上再亏待我妈了,钱没了可以再挣,我妈只有一个。”
这话我说得真心实意,也希望能堵住她的嘴。
姑妈沉默了一会儿。
“行吧,你有孝心是好事。”
她站起身,走到阳台。
“我看看你妈那盆君子兰,被你养得怎么样了。”
我的后背瞬间绷紧了。
那盆花,在“收获”了第一根金条后,我发现它中间又开始冒出了一个新的、小小的金点。
我死死地盯着姑妈的背影。
她拨开我用来遮挡的那些绿植,走到了君子兰面前。
“哟,还行嘛,没死,还长新叶子了。”
她嘀咕着。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那个金点,现在只有一粒芝麻那么大,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幸好,姑妈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宽大的叶子上。
她摸了摸叶片,又扒拉了一下盆里的土。
我突然想起来,那些发霉的茶叶末,还混在土里。
“你这土里掺的什么?黑乎乎的。”
她捻起一点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一股霉味儿。”
她嫌弃地拍了拍手。
“就是些烂树叶,当肥料的。”
我赶紧说。
“城里孩子就是没见识,烂树叶哪能当肥料。”
她教训了我一句,就没再理会那盆花。
她从阳台走回来,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承川说他想换辆车,你看……”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姑妈,我真的没钱,我借的钱都要还的。”
“行行行,知道了,小气鬼。”
她不满地嘟囔着,拿上包准备走。
走到门口,她又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佳禾,有好事要记得跟家里人分享,别一个人藏着掖着。”
门关上了。
我靠在门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后背已经湿透了。
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姑妈的怀疑,已经像一颗种子,种下了。
04 怀疑的裂痕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像个双面间谍。
在医院,我是孝顺女儿,悉心照料着我妈。
回到家,我就是个秘密的守护者,每天雷打不动地观察那盆君子兰。
第二根金条长得比第一根要慢一些。
大概花了十天,才长到差不多的大小。
我用同样的方法“收获”了它,换来的钱,一部分存起来,作为我妈后续治疗的备用金,另一部分,我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不想再过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拮据日子了。
我妈的病需要钱,更需要好的心情和营养。
我给她请了一个专业的护工,分担我的一部分压力。
我还买了很多专业的康复器材,让她在家里也能做一些简单的恢复训练。
这一切,自然没能逃过姑妈的眼睛。
那天,我去医院给我妈送饭,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姑妈的大嗓门。
“……姐,不是我说你,你得好好问问佳禾。她一个普通上班的,哪来这么多钱?又是请护工,又是买这些乱七八糟的器械,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是我让她买的。”我妈的声音很平静,“她预支了工资,又跟朋友借了点。”
“又是借?她有多少朋友够她这么借的?你别太天真了!”
姑妈的语气很激动,“我跟你说,我昨天去缴费处问了,佳禾给你交的那个进口药,一次就交了半年的,六万多!她一个总监能借给她这么多钱?当我们是傻子吗?”
我推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她竟然真的去查了。
“你别管钱是哪儿来的,只要是正道来的就行。我女儿我了解,她不会做坏事的。”
我妈还在维护我。
“哼,知女莫若母?我看未必。”
姑妈冷笑一声,“别是找了个有钱的老头子,被人家包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妈气得咳嗽起来。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猛地推开门。
“姑妈!”
姑妈看到我,一点也不尴尬,反而理直气壮地看着我。
“哟,说曹操曹操就到。佳禾,你来得正好,你跟你妈解释解释,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看着我妈气得通红的脸,心里的火“蹭”地一下就上来了。
“姑妈,这是我的私事,您没必要打听得这么清楚吧?”
“什么叫你的私事?你是我亲侄女,你妈是我亲姐姐,你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
她叉着腰,一副大家长的派头。
“我怕你年纪轻轻,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我没被骗。”
我走到我妈床边,轻轻拍着她的背,“您也别瞎猜了,钱是我凭本事挣的,干干净净。”
“凭本事?就你那一个月几千块的工资?”
姑妈一脸不信。
“您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
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
姑妈看我油盐不进,气得直翻白眼。
她大概也觉得在病房里吵架不好看,撂下一句“好心当成驴肝肺”,就气冲冲地走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忧心忡忡。
“佳禾,你跟你姑妈……唉。”
“妈,您别管她,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我安慰着我妈,心里却知道,这道裂痕,已经越来越大了。
更大的冲突,在我拒绝了表弟陆承川之后,彻底爆发了。
那天我刚下班回家,陆承川就堵在了我家门口。
他穿着一身潮牌,头发抹得油光锃亮,靠在他那辆二手宝马旁边,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姐,下班了?”
“有事?”
我对他向来没什么好脸色。
“也没什么大事。”
他绕着我走了一圈,眼神像在评估一件商品。
“听说你最近发财了?”
“听谁说的?”
“我妈呗。”
他撇撇嘴,“姐,你这就没意思了啊。发了财,也不知道照顾照顾弟弟。”
“我没发财。”
“行了,别装了。”
他有些不耐烦,“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看中了一套房子,首付还差五十万。你先借我,等我以后赚了钱,双倍还你。”
我简直要被他气笑了。
五十万。
他真敢开口。
“我没有五十万。”
“不可能!”
他一口咬定,“我妈都算过了,你又是请护工又是交药费的,没个百八十万你根本撑不起来。五十万对你来说,就是毛毛雨。”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我的语气冷了下来,“陆承川,我不管你听谁说了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借给你。”
“阮佳禾!”
他急了,上前一步拦住我,“你别给脸不要脸!那钱是不是你找野男人要的?你信不信我把这事捅出去,让你在小区里都抬不起头!”
“你敢!”
我瞪着他。
“你看我敢不敢!”
他一副无赖的嘴脸,“五十万,买我闭嘴,很划算吧?”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无比恶心。
这就是我姑妈教出来的好儿子。
“我再说一遍,我没钱。”
我绕开他,拿出钥匙准备开门。
“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报警,告你诽谤。”
陆承川没想到我态度这么强硬,愣了一下。
“行,阮佳禾,你够狠!”
他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给我等着!”
说完,他钻进他的破宝马,一脚油门,轰鸣着开走了。
我知道,他肯定会回家添油加醋。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等着我。
果然,那天晚上,姑妈的电话就打来了。
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说我没人情味,说我有了钱就六亲不认,说她白疼我这么多年了。
我一句话没说,等她骂累了,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关机。
我走到阳台,看着那盆君子兰。
第三根金条的嫩芽,已经破土而出,在夜色里,闪着微弱又坚定的光。
我轻轻摸了摸它。
这是我的底气。
既然他们不肯放过我,那就别怪我,不念亲情了。
05 摊牌
我以为他们会消停几天。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直接杀上了门。
姑妈,姑父,还有陆承川。
姑父是个老实人,平时在家基本说不上话,今天也被拉来壮声势了。
我打开门,看着他们三个黑着脸站在门口,就知道今晚没法善了了。
“佳禾,我们要跟你好好谈谈。”
姑妈推开我,带着一家人浩浩荡荡地进了屋。
我妈听到动静,也从房间里出来了。
“姐,姐夫,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再不来,这个家就要被某些人给败光了!”
姑妈阴阳怪气地说,眼睛一直剜着我。
“都坐吧。”
我关上门,平静地给他们倒了三杯水。
“有什么事,就说吧。”
“阮佳禾,我问你,你是不是发了一笔横财?”
姑妈开门见山,声音又尖又利。
“是。”
我看着她,干脆地承认了。
事到如今,再否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姑妈大概是准备了一肚子的质问和逼迫,没想到我这么轻易就承认了,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你……你承认了?”
“对,我承认了。”
我点点头。
“钱是哪儿来的?”
姑妈立刻追问。
“这个,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陆承川激动地站了起来,“是不是来路不正?我就知道!”
“承川,你坐下!”
姑父拉了他一把,然后看着我,语气还算温和。
“佳禾,你跟姑父说实话,这钱……干净吗?”
“姑父,您放心,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我对姑父,还保留着一丝尊重。
“既然是干净的,为什么不能说?”
姑妈不依不饶,“你是不是怕我们跟你借钱?”
“对。”
我又承认了。
这下,姑妈的脸彻底挂不住了。
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
“你……你这个白眼狼!我们老阮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有了钱,连亲戚都不要了!”
“姑妈,”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从小到大,您是怎么对我们母女的,您自己心里清楚。”
“小时候,承川的压岁钱,您都给他存着,我的压岁钱,您说替我妈保管,再也没还过。”
“后来,您家里换下来的旧冰箱、旧电视,都说是送给我们,转头就跟我妈要‘折旧费’。”
“前段时间,您拿来那盒发霉的茶叶,说是好东西,转脸就跟承川说,打发叫花子呢。”
我每说一句,姑妈的脸色就白一分。
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太久了。
“你……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说过!”
她嘴硬道。
“您说没说过,您自己知道,我也知道。”
我平静地看着她,“所以,这笔钱,跟您,跟我表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妈的救命钱,我一分都不会给别人。”
“反了你了!”
姑妈猛地一拍桌子,“那笔钱,本来就该有我们家一份!”
“为什么?”
我问。
“因为……”
姑妈眼珠子一转,突然指着阳台的方向。
“因为那笔财,是用我给你的东西换来的!”
我的心,猛地一沉。
她知道了?
不可能。
她是怎么知道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姑妈看我变了脸色,更加得意了。
“你最近天天往阳台跑,把那盆破花当宝贝一样供着。我上次来就觉得奇怪,那土里,不就是我送你那盒茶叶的茶末吗?”
她竟然,真的记住了那个细节。
“我送你的茶叶,是‘引子’,那盆花是‘财神’!阮佳禾,你发的这笔财,是我给你带来的!你说,该不该分我们一半?”
她这番话说得漏洞百出,荒唐可笑。
什么“引子”,什么“财神”,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她歪打正着,竟然猜中了最核心的秘密。
我看着她那张贪婪又笃定的脸,再看看旁边同样两眼放光的陆承川。
我突然明白了。
跟他们讲道理,是行不通的。
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既然如此……
我心里一个计划,慢慢成形。
我沉默了许久,然后,抬起头,露出一副被说中心事、惊慌失措的表情。
“你……你怎么知道的?”
“哈!我果然没猜错!”
姑妈看我这反应,兴奋地大叫起来。
“真的是那盒茶叶?”
陆承川也凑了过来,满脸的不可思议。
“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低下头,声音带着哭腔,“我就是把那茶叶倒进花盆里,它……它就长出金子来了。”
“长出金子?”
一家三口,异口同声。
“嗯。”
我点点头,装作不情不愿地,把他们带到阳台。
第三根金条,已经有小拇指那么长了。
在灯光下,金灿灿的,格外诱人。
姑妈和陆承川的眼睛,瞬间就直了。
他们扑到花盆前,像是两头饿狼看到了鲜肉。
“天哪……真的是金子……”
姑妈伸手想去摸,被我一把拦住。
“别碰!一碰就不灵了!”
我胡说道。
姑妈赶紧缩回手,但眼睛还是死死地黏在那根金芽上。
“佳禾啊……”
她的声音,瞬间变得无比温柔,温柔得让我起鸡皮疙瘩。
“你看,姑妈就说吧,咱们是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
“这茶叶是姑妈给你的,这财运,自然也有姑妈的一半。”
“不,不是一半!”
陆承川突然开口,“妈,这茶叶是咱家的,这花就等于是用咱家的东西种出来的,长出来的金子,当然也都是咱家的!阮佳禾她只是代管!”
我看着这对母子一唱一和,心里冷笑。
贪婪,真是没有止境。
“那你们想怎么样?”
我“怯生生”地问。
“很简单。”
姑妈清了清嗓子,“这盆花,我们带走。以后长出来的金子,都归我们。作为补偿,你妈的医药费,我们包了。”
她算盘打得真精。
用我自己的钱,给我妈治病,还想落个好名声。
“不行!”
我立刻拒绝,“这花认生,离了我,它就不长了。”
“胡说!明明是认茶叶!”
陆承川反驳道。
“对,是认茶叶!”
姑妈眼睛一亮,她想起了什么。
“我记得,当时别人送我的是一大箱,我就给了你一盒。我家里,应该还有!”
【伏笔照应#3】。
我心里一动,知道鱼儿要上钩了。
“真的吗?”
我装出惊喜的样子。
“当然!”
姑妈得意地说。
“那……”
我咬着嘴唇,犹豫了半天,才下定决心似的说。
“那这样吧。这盆花不能动。我这里,还有最后一包那种茶叶,是我偷偷藏起来的。”
我从厨房一个不起眼的柜子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
里面,是我从网上买的,最普通的、已经发了霉的茶叶。
“这是最后一包了。你们拿回去,找个花盆试试,要是也能长出来,那这财运就是你们的。要是长不出来……那你们以后,就别再来烦我了。”
我把那个纸包,递到姑妈面前。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和算计。
她不相信我。
她觉得我肯定还有私藏。
她想要更多的,她想要全部。
她想要那盆会下金蛋的“母鸡”。
“一言为定?”
她接过纸包,掂了掂。
“一言为定。”
我看着她,郑重地点点头。
他们拿着那个茶叶包,心满意足地走了。
临走前,姑妈的眼神,又深深地看了一眼阳台那盆君子兰。
我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想要的,是釜底抽薪。
而我给她的,正是一个让她自投罗网的机会。
06 收网
送走姑妈一家,我立刻反锁了门。
我妈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脸担忧。
“佳禾,你真的把……那个秘密告诉他们了?”
“妈,您放心,我自有分寸。”
我扶着她坐下,“今晚您跟我一起睡吧。”
我没告诉我妈全部的计划,我怕她担心。
我只是告诉她,那盆花很神奇,但需要特定的“照料”。
接下来的两天,风平浪静。
姑妈一家没有再来骚扰我。
我用手机上的监控软件,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根金条在一点一点地长大。
同时,我也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关于入室盗窃的法律条款。
我知道,姑妈手里的那把备用钥匙,将是她最大的罪证。
【伏笔揭晓#2】。
第三天,我算着日子,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我特意换了身衣服,对我妈说:“妈,我今天约了王阿姨她们出去逛逛公园,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护工会照顾您的。”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然后拿着包,像往常一样出了门。
但我没有走远。
我只是下楼,坐进了小区对面咖啡馆的窗边位置。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那栋楼的单元门。
我在手机上,点开了那个对着阳台的监控画面。
【伏笔揭晓#1】。
一切准备就绪。
我在等。
等那条鱼,自己游进网里。
上午十点半左右,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是姑妈。
她一个人,戴着口罩和帽子,鬼鬼祟祟地走进了我们单元。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我点开监控,把音量调到最大。
几分钟后,我家的门,传来了轻微的钥匙转动声。
然后,是门被打开的声音。
姑妈的身影,出现在了客厅里。
她蹑手蹑脚,先是探头到我妈的房间看了一眼,护工正在给我妈按摩腿,两人在轻声聊天,没有发现她。
她松了口气,然后直奔阳台。
监控画面里,她的脸因为激动和贪婪而显得有些扭曲。
她拨开那些遮挡的绿植,一眼就看到了那盆君子兰。
上面的那根金条,已经长到了十几厘米长,金光闪闪,比我之前“收获”的任何一根都大。
这是我故意留给她的。
“我的……都是我的了……”
我能听到她压抑着的、兴奋的喘息声。
她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抱起了那盆花。
很沉。
她抱得有些吃力。
但她没有放弃。
她还不忘把那个我给她的、装着假茶叶的牛皮纸包,扔在了我家的鞋柜上。
大概是想伪造一个“物归原主”的假象。
她抱着花盆,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出了我家。
监控画面里,只剩下空荡荡的阳台角落。
我看着她走出单元门,上了一辆出租车,消失在街角。
我拿出手机,按下了三个数字。
“喂,110吗?我要报警,我家……被盗了。”
警察来得很快。
我赶回家的时候,他们正在现场取证。
我“惊慌失措”地向他们描述了失窃的经过。
“……我最重要的,就是我妈留下的一盆君子兰,那是我爸去世前送给我妈的,对我们意义非凡。小偷什么都没拿,就偷了那盆花!”
我边说边掉眼泪,演得自己都快信了。
“您别急,”一位年轻的警察安慰我,“我们已经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很快就会有线索的。”
“警察同志,”我抽泣着说,“我……我怀疑是我姑妈。”
“哦?为什么这么说?”
“她有我家的备用钥匙,而且她之前就一直念叨我这盆花,说长得好,想搬走。”
“她有你家钥匙?”
警察的表情严肃起来。
“嗯,她以前说方便照顾我们,自己去配的。”
“好的,我们了解了。您放心,我们会依法处理的。”
我静静地等待着。
我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场。
一个小时后,我的手机响了。
是派出所打来的。
“阮女士吗?我们已经找到了您的姑妈程筝女士,也找到了您说的那盆花。现在需要您过来一趟,核实一下情况。”
我挂了电话,深吸一口气。
收网的时刻,到了。
我赶到派出所的时候,姑妈、姑父、陆承川都在。
姑妈正激动地跟警察比划着什么。
“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这花不是我偷的!这是我侄女自愿给我的!我们说好了的!”
那盆君-子兰,就摆在桌子中间。
“程筝女士,我们有监控录像,显示您是趁阮女士不在家时,用钥匙开门进去,将花盆抱走的。这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入室盗窃。”
警察冷静地说。
“我没有!我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姑妈急了,她指着那盆花,“这花能长金子!是用我的茶叶种出来的!不信你们看!”
她说着,就伸手去扒拉那根金条。
“妈,别急!”
陆承川也凑上去,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对着那根金条照来照去。
“警察叔叔,你们看,真的是金子!纯金的!”
办公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根金条上。
一个年长的警察走过来,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那根“金条”。
他用指甲在上面轻轻刮了一下。
一层金色的漆,被刮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灰白色的,塑料的质地。
“……”
陆承川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
姑妈的眼睛,瞪得像铜铃。
“这……这怎么可能?”
她不敢相信,扑上去,用手使劲地抠那根“金条”。
金色的油漆,一片一片地剥落。
露出来的,是一根做得惟妙惟肖的,塑料棒。
是我从网上买的模型,自己喷的漆。
“假的?怎么会是假的?”
姑妈瘫坐在地上,失魂落魄。
“我亲眼看到的……明明是真的……”
“程筝女士,”警察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现在,人赃并获。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那张瞬间苍老了十岁的脸,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慢慢走进去。
“姑妈。”
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看到我,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不解。
“是你……是你设计我!”
“我设计你什么了?”
我一脸无辜,“我只是报了个警,说我爸留给我妈的遗物被偷了。我可没说它会-长金子。”
“至于您说的茶叶……”
我指了指她扔在我家鞋柜上的那个牛皮纸包。
“那包茶叶,我已经交给警察同志了。里面就是普通的、发霉的茶叶而已。”
“是你!都是你这个小贱人!”
她疯了一样想朝我扑过来,被警察一把按住。
“阮佳禾!你不得好死!”
我看着她疯狂咒骂的样子,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
“姑妈,你用备用钥匙开我家的门,不是第一次了吧?”
她的咒骂,戛然而止。
07 新生
姑妈因为入室盗窃,证据确凿,被依法拘留了。
数额虽然不大,但因为是入室,性质就变了。
姑父为了给她办理取保候审,到处求人,头发都白了一半。
陆承川那辆二手宝马也卖了,凑钱请律师。
他们一家,彻底成了小区里的笑话。
听说姑妈出来后,大病了一场,整个人都蔫了。
再也没人见过她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妈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后,抱着我,哭了很久。
她说:“佳禾,是妈没用,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我摇摇头:“妈,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我用剩下的钱,给我妈安排了最好的康复治疗。
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已经能拄着拐杖,在病房里慢慢走动了。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把那盆真正的君子兰,搬到了我妈的病房窗台上。
它在“休眠”了一段时间后,又在中心的位置,冒出了一个新的、小小的、金色的光点。
我妈看着那个光点,眼神里没有了贪婪和恐惧,只有一种经历过风雨后的平静。
“佳禾,把它扔了吧。”
她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
“妈?”
“这种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留着,不是福气,是祸根。”
她拉着我的手,认真地看着我。
“我们不需要它了。以后,妈陪你,我们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看着我妈,她的眼睛在阳光下,清澈又明亮。
我点了点头。
“好。”
我当着我妈的面,把那盆君子兰,连同里面的土,一起倒进了医院楼下的垃圾桶里。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身上某个沉重的枷锁,突然就消失了。
回到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暖洋洋的。
我妈正在修剪一盆护士送来的普通水仙。
叶片青翠,花苞饱满,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走过去,和我妈并排站在一起。
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是要靠我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但这一次,我不再害怕了。
真正的财富,从来都不是花盆里长出的金子。
而是摆脱了那些吸血的亲情,掌握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和所爱的人一起,迎接每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清晨。
那才是真正的新生。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